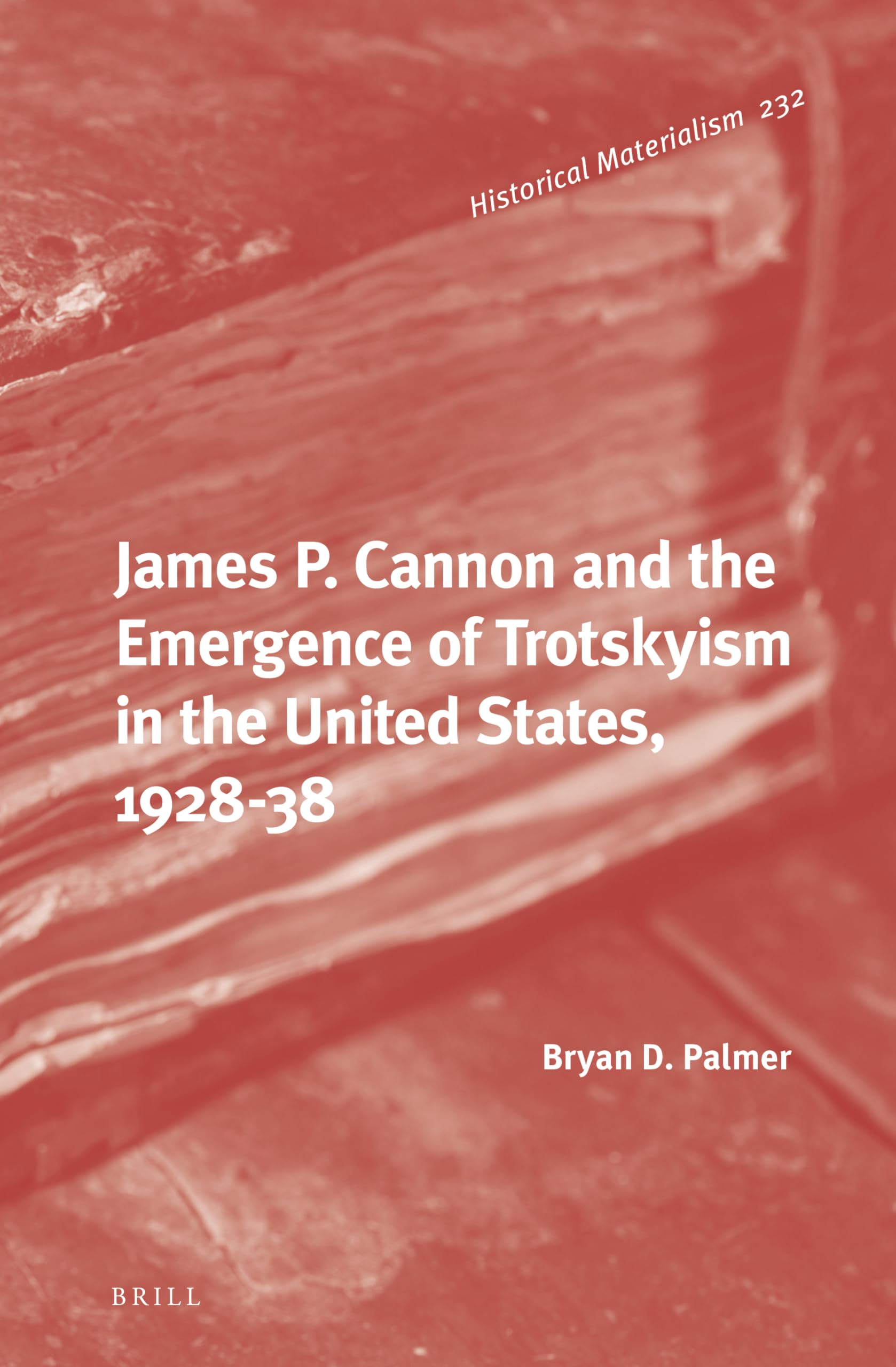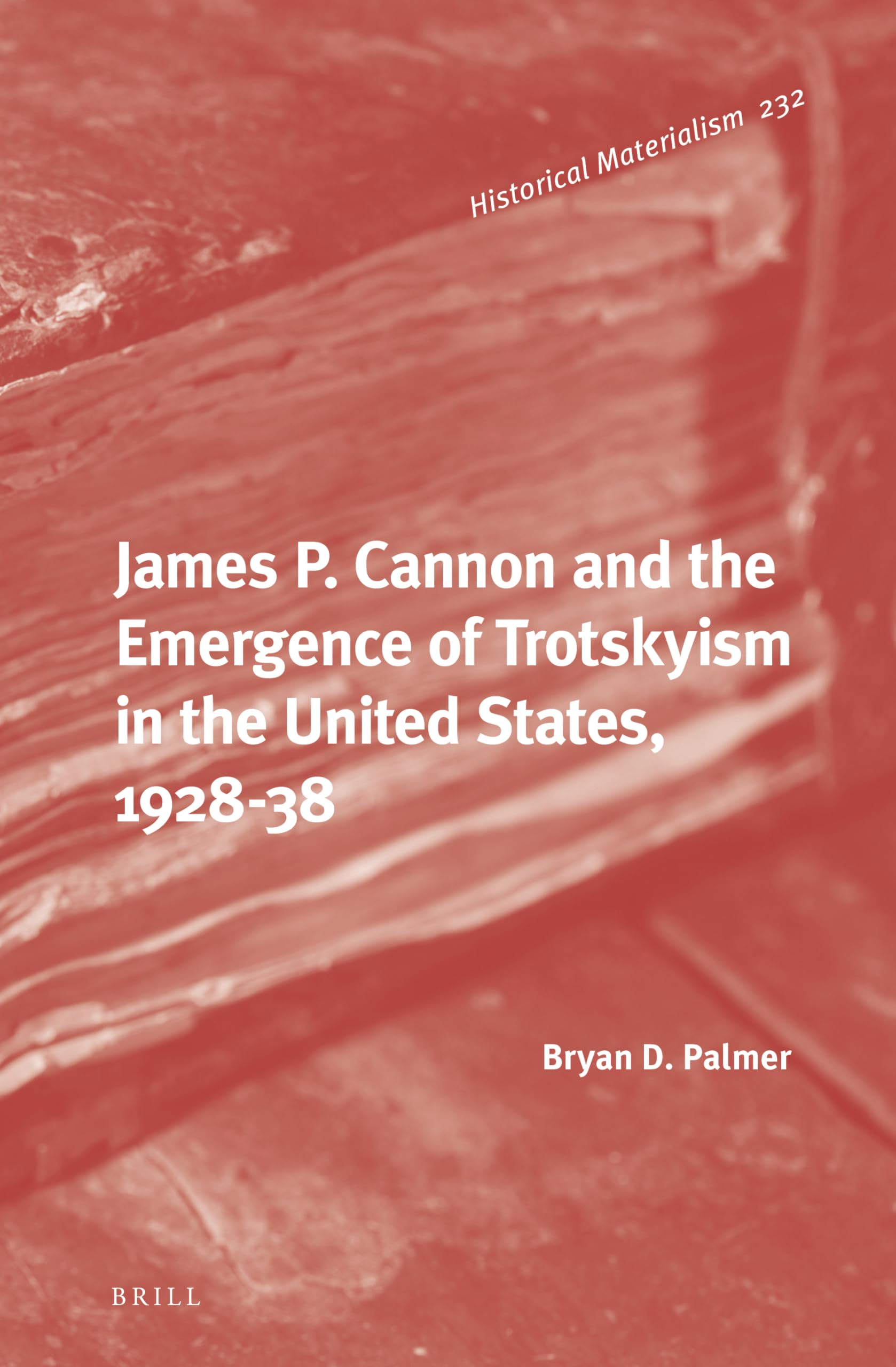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詹姆斯·P·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先驱
﹝美国﹞默里·史密斯(Murray Smith)
2022年12月30日
Jiaze E 翻译;匡红、素侠云雪 校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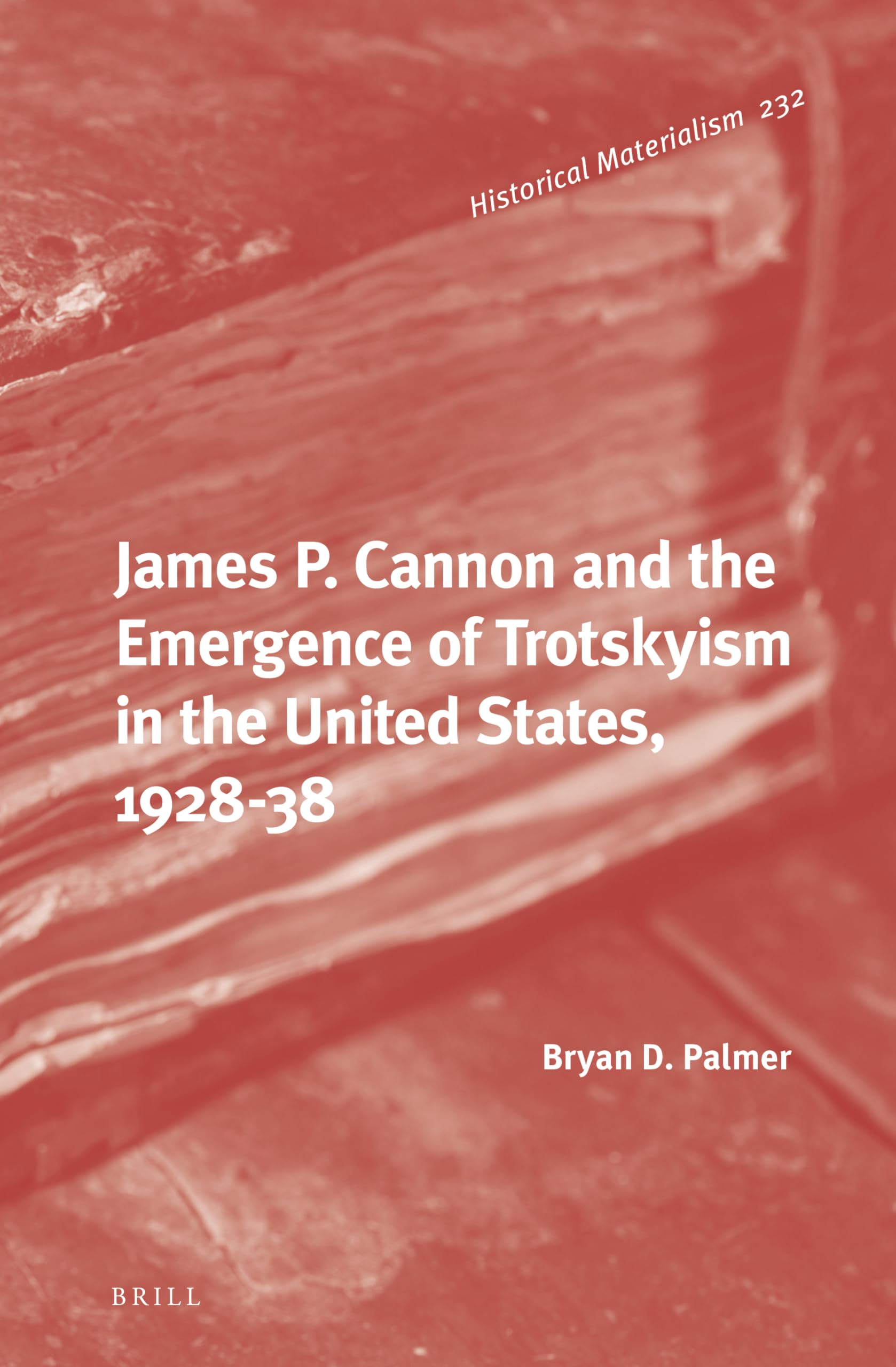
《詹姆斯·坎农与托洛茨基主义在美国的兴起,1928-38》
布莱恩·帕尔默(荣誉退休教授,特伦特大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劳工和社会史的贡献不仅丰富多彩,而且令人印象深刻。但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他最持久的贡献可能是对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先驱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 Patrick Cannon)生平和时代的不朽描述。坎农可以说是美国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革命社会主义政治家,但同时也是美国劳工史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史上被严重忽视的人物。
帕尔默关于坎农的预计的三部曲的第一部已于2007年由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出版。《詹姆斯·坎农和美国革命左派的起源,1890—1928》(James P. Cann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Left, 1890-1928)作为对美国早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的重要贡献,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帕尔默敏锐地描述了坎农作为一名年轻的革命者的职业生涯,他最初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的组织者,然后是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领导的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的左翼领导人,随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之后成为美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CPUSA))的创始领导人。坎农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直到1928年被美国共产党驱逐出党之前,一直是一名著名的杰出的共产党员——最为人所知的是共产党的第一任主席的身份,以及他对工会和劳工保卫工作(labour defense work)的贡献——他也是党内福斯特—坎农派系(Foster-Cannon faction)的关键领导人。
经过漫长的等待,第二卷,《詹姆斯·坎农与托洛茨基主义在美国的兴起,1928—1938》(博睿Brill,2021;干草市场Haymarket,2022)终于出版了,而且没有让人失望。这部新作的确极大地丰富了现在必然被认为是一部力作的作品——传记文学体裁的杰作,同时也是一部具有深远历史和政治意义的作品。在这些方面,帕尔默关于坎农的两卷本已经可以与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所著的俄罗斯革命领袖列夫·托洛茨基的经典传记相媲美,后者是一部三部曲,出版时间跨度为1954年至1963年的九年间。此外,在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创性研究的深度以及政治敏感性和判断力的合理性方面,帕尔默的坎农传记(尚待完成)可以说已经超越了多伊彻那部广受赞誉的作品。
作为坎农的长期崇拜者和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帕尔默的这本新书只能被看作是献给所有声称支持当代全球社会主义变革的人们的一份珍贵礼物。因为坎农在上世纪30年代努力打造的一个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故事对于今天所有从事类似斗争的人来说,都充满了至关重要的启示,无论那些声称继承托洛茨基遗产的五花八门的组织持何种观点,即使他们在从中国国家的阶级性质到乌克兰战争等各种问题上宣传的立场大相径庭。
吉姆·坎农后世最忠实的崇拜者之一(已故的詹姆斯·罗伯逊(James Robertson))曾经说过,吉姆·坎农在他的全盛时期展示了成为“北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能力。然而,对于这种赞誉,坎农本人很可能会将其视为不受欢迎的偶像崇拜,因为他蔑视任何可能成为共产主义领袖的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个人主义政治或崇拜主义。正如帕尔默所指出的那样,在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主义使苏联和(第三)共产国际堕落,以及随后为建立新的革命共产主义第四国际而奋斗的过程中,坎农始终坚持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共同信念,即革命组织只能建立在集体领导、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和国际主义观点的基础上。
在寻求建立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工人党的过程中,坎农面临着许多巨大的障碍:资源的匮乏,斯大林主义对手的强烈敌意,美国资本主义国家的镇压机器,无原则的小团体主义和官僚消极主义,以及他最亲密的合作者中的宗派主题倾向,还有就是他自己的个人问题和缺点。然而,当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 SWP)于1937年12月31日成立的时候,作为托洛茨基即将成立的第四国际组织的美国分支,坎农已经成为一个组织的卓越领导人,这个组织具有经过考验的集体领导,充满活力的内部生活,在阶级斗争的许多领域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原则的革命工作记录,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项目。这个计划是托洛茨基与坎农和其他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密切磋商制定的,是第四国际的基础文件,它不仅提炼了俄国革命和左翼反对派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托洛茨基将其定义为在社会化财产形式基础上的官僚—寡头统治的社会现象)的基本教训,还提炼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阶级斗争中的实践经验。
吉姆·坎农、文森特·雷·邓恩(Vincent Ray Dunne)、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法雷尔·多布斯(Farrell Dobbs)以及其他美国托洛茨基主义领军人物为被称为《过渡纲领》的这一宣言所做的贡献值得给予最充分的认可;该纲领在当今和未来的革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持久核心地位也应得到最充分的认可。这份文件不仅囊括了共产国际——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9年至1922年间的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编纂的最有价值的纲领性和战略性概念;它还扩展、完善并在重要方面巩固了这些思想。第四国际的这一基本纲领第一次明确地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实践建立在一个清晰的过渡要求体系之上——这一体系在工人阶级(及其潜在盟友)的防御性和局部斗争与实现工人权力——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作为一个整体,《过渡纲领》预见并预示了工人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早期阶段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内容,与乌托邦式的改良主义计划果断决裂,这些改良主义计划通过资产阶级民主渠道逐步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或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将资本主义重建为一个更加人道、民主和理性的制度。
有鉴于此,帕尔默对坎农在1928年至1938年这一动荡时期作为托派领袖的政治历程的描述采用了手册的形式——尽管这本手册大约有一千二百页,非常长!这本手册主要讲了如何建设一个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及其被压迫的同盟的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工人统治的严肃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
坎农曾经写道:“政治是在正确的时间采取正确行动的艺术。”在他的领导下,在托洛茨基的远程的不可估量的指导下,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迎来了“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的挑战。帕尔默在长达六章的篇幅中雄辩而详细地描述了坎农和他的同志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他们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并附上了一个引言和一个实质性的结论。在这里对如此庞大和深入研究的作品作出公正的评价显然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对其中一些最突出的政治主题和议题的调查,我们可以对该书的范围和重要性有所了解。
第一章,题为“一个美国左翼反对派”(An American Left Opposition),接续了“1890-1928”卷的结尾:坎农、沙赫特曼和加拿大共产党人莫里斯·斯佩克特(Maurice Spector)为托洛茨基在《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The Draft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 Criticism of Fundamentals)中提出的论点而进行的斗争。这份文件被约瑟夫·斯大林压制,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由坎农和斯佩克特偷运出俄国,使斯大林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学说遭到毁灭性的批评,同时也揭露了共产国际在欧洲(包括背叛1926年英国大罢工)和中国(使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高潮屈从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导致1927年上海公社的血腥失败)的政策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托洛茨基的文件重申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战略目标,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拒绝与资产阶级的所有政治联盟,宣布国际左翼反对派(International Left Opposition, ILO)的成立,致力于回归早期共产国际的政策和观点,坚决反对斯大林主义者将世界共产主义变成苏联官僚机构外交政策和外交工具的“民族改革”的努力。此外,它还呼吁明确接受托洛茨基长期坚持的“不断革命”理论——该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衰落的时代,“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发挥进步作用,每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无论是在发达国家的国土上开始,还是在更加落后的国土上开始,都只能在世界舞台上完成。因此,一个取得胜利的工人国家的责任是支持所有土地上的工人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而不是以牺牲这些斗争为代价寻求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和解(和平共处)。
坎农及其思想家们宣布支持托洛茨基,导致他们迅速被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以极其不民主的方式驱逐出党,党内掀起了一场针对他们的诽谤运动,以及针对他们最初为国际左翼反对派争取仍在寻求改革的党的内外追随者的努力的诽谤运动。这些努力最终导致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 CLA)的形成,它公开宣布为共产党的党外派别,拥有自己的报纸《战士报》(The Militant)和一个适度的图书出版计划。一开始,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只有一百多名成员——主要集中在纽约、明尼阿波利斯、波士顿和多伦多——但由于有资深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其中包括安托瓦内特·科尼科(Antoinette Konikow)、阿内·斯瓦贝克(Arne Swabeck)、文森特·邓恩(Vincent Dunne)和卡尔·斯科格伦德(Carl Skoglund)),几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和演说家,以及一批身经百战的工会战士,他们对国际劳工组织的理念坚信不移,因此弥补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人数和物质资源上的不足。
除此之外,帕尔默对这段历史的处理揭示了美国共产党领导层和美国共产党党员队伍在多大程度上被斯大林和共产党强加给他们的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腐化——这次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涉及对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诽谤、入室行窃和身体暴力。通过对成功的工人斗争和其他活动的领导,共产党保留了大多数有志于革命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忠诚,但它对工人民主政体基本原则的背叛是显而易见的,这玷污了它在更广泛的工人运动中的声誉,并加强了它内部的“斯大林化”,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破坏性后果。
第二章,题为“大热天”(Dog Days),重点讲述了大萧条的早期以及由此带来的阶级斗争低潮。此章特别用大量篇幅探讨了造成士气低落的物质和心理条件,这些条件导致了坎农与共产国际年轻一代领导人(沙赫特曼、斯佩克特和阿伯恩)之间有害的派系裂痕,以及托洛茨基(当时流亡土耳其)为防止共产国际内讧而进行的远距离干预。除此之外,帕尔默还讨论了随着斯大林主义向快速工业化以及苏联农业强制集体化的共产国际政策的戏剧性转变。从1929年开始的将近五年里,斯大林主义者采取了一种极左的宗派政策,使托洛茨基主义者将他们描绘成机会主义的“官僚中派主义”的形象复杂化,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政策为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在此期间,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优先宣传托洛茨基对法西斯主义的精辟分析,以及他呼吁德国工人阶级党派(尤其是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战斗性联合战线,以阻止希特勒上台(1933年1月30日通过)。德国斯大林主义者谴责社民党(它寻求与反纳粹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议会联盟)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嘲笑托洛茨基的警告是“反革命”,并奉行阻止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对抗法西斯威胁的政策。随后,共产党未能组织任何有意义的反对纳粹政权巩固的斗争,加上斯大林主义者坚持共产党的政策一直是正确的,导致托洛茨基得出结论,共产国际作为一支革命力量已经结束。从此以后,革命者的任务不再是改良共产国际(或实际上其苏联统治部门),而是为一个新的国际奠定基础。
这种重新定位对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及国际左翼反对派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意味着剥夺争取共产党的优先权,重新关注与左倾的社会民主主义或“中派主义”潮流的接触和潜在融合,同时在一个新的旗帜下开展自己的独立运动。现在的目标是促进“重组”进程,以期发起第四国际。这一进程的先锋是托洛茨基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这本书剩余章节的主题是这种新的取向如何发挥作用,并为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带来了重大成果。
在第三章,题为“日光:分析与行动”(Daylight: Analysis and Action),帕尔默深入研究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为解决一系列重要问题而精心制定的新的和创新的方法:以工会为基础的劳工党运动(这个问题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共产主义者中引起了很多混乱和争论);在美国反对黑人压迫的斗争中的革命政策(斯大林主义者在他们极左的“第三时期”期间,把这个问题看作是黑人的“民族自决”——甚至是分裂——问题,而不是一个需要为种族平等进行革命斗争、最终形成工人政府的问题);以及由于经济萧条而出现的失业工会内部和周围的工作策略,还有坎农作为美国共产党领导人专门从事的那种劳工保护工作。
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也更多地参与工会工作,尽管结果喜忧参半。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个领域的第一次重大尝试是1934年1月的纽约酒店工人工会运动和大罢工,由多变的B·J·菲尔德(B.J. Field)领导(或者说是误导),他是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知识分子,因为对罢工处理不当和违反党的纪律而被开除。幸运的是,菲尔德的惨败很快被同年真正鼓舞人心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反抗运动所掩盖,在这场运动中,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最老练的工会战士(包括邓恩兄弟和坎农本人)起到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
第四章“明尼阿波利斯的战士”(Minneapolis Militants)完全致力于这场重大的劳工起义——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斗争,以及旧金山码头工人的罢工和托莱多汽车工人罢工,标志着1934年是产业工会运动在北美起飞的一年。这一章广泛引用了帕尔默早期的著作《革命卡车司机》(Revolutionary Teamsters, 2014),但也包括了一些关于斗争的重要新材料,这些材料展示了北美有史以来最先进的阶级斗争方法。从本章各小节的标题可以看出所涵盖的广泛领域:“总罢工”、“卡车司机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宣传的老鼹鼠”、“煤场罢工的教训”、“罢工准备、失业者鼓动和产业工会主义”,“女士/妇女的辅助组织”,“论坛巷密谋和代表之战运行”,“1934年5月:定居点安全,胜利推迟”,“斯大林主义者的诽谤”、“农民-工人两阶级混合还是阶级斗争的观点”、“宣布罢工,阴谋暴露”、“血腥星期五,戒严/红色恐慌”和“突然的意外胜利”。
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胜利,尽管有残酷的国家镇压(曾一度动员国民警卫队),卡车司机工会全国领导层也扮演了背信弃义的角色,却的确为公路上有组织的运动奠定了基础,这场运动不仅将运输工人的地理覆盖范围扩展到了整个美国中西部地区,而且是在工业而非手工业的基础上进行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领导者再次发挥了作用,尤其是法雷尔·多布斯的领导作用。多年后,吉米·霍法(Jimmy Hoffa)称赞多布斯是这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
第五章,题为“打入策略”(Entryism),讲述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与A·J·穆斯特(A.J. Muste)领导的左翼中派主义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 Workers Party, AWP)的融合,以及工人党的组建,以及后者随后加入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领导的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 SPA)的故事。美国工人党的“穆斯特派”提供了在俄亥俄州获胜的托莱多汽车罢工的领导核心,这次罢工是有组织的劳工的一次关键胜利,为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和产业工会联合会(CIO)铺平了道路。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与美国工人党于1935年的融合不仅大大增加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份量和威望,同时也为更大胆地发展托洛茨基运动的尝试奠定了基础。通过运用托洛茨基敦促他的法国追随者对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即法国社会党)实施的“打入策略”,坎农和大多数工人党领导人认为,他们可以赢得美国社会党成员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使之转入革命社会主义。但是这个计划也遭到了少数派(宗派主义的欧勒派(Oehlerites))的强烈反对,他们最终离开了党。帕尔默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探讨了这场围绕所谓“法国转向”策略的斗争,这种方式表明,该党在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里足以弥补在采用这一策略的损失。
斯大林主义者转向亲罗斯福的立场,这符合共产国际推动阶级合作主义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新政策,为美国社会党在激进的工人和年轻人中扮演可行的、左翼的、可替代美国共产党的角色开辟了空间。坎农的工人党看到并抓住了机会。在向美国社会党领导层做出某些组织上的让步以获准加入该党之后,他们很快就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核心小组在党内运作,拥有自己的报纸《社会主义呼吁》(Socialist Appeal),参与建设该党,同时也推进自己的议程。
与此同时,改良派/中派的美国社会党领导层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在一个关键问题上,观点的危机正在迅速发展:美国社会党是应该保持其坚定反对资本主义民主党的传统立场(德布斯派),还是应该屈服于日益增长的压力,加入斯大林主义者的阵营,尽管是非正式的,支持民主党总统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加入加剧了这种正在出现的裂痕,他们向美国社会党的全体党员提出了另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向右转,接受阶级合作,还是急剧向左转,接受坎农团体成员所倡导的阶级斗争纲领。最后,美国社会党领导人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摆脱托洛茨基主义者,但当他们最终做到这一点时,他们失去了数百名成员,以及他们青年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可以说,从1936年中期到1937年秋末,这种短期加入美国社会党的做法,无疑是世界托洛茨基主义历史上“打入策略”最成功的应用。
第六章“审判、悲剧和工会”(Trials, Tragedies and Trade Unions)与前一章所涵盖的时期重叠,同时深入研究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他们选择优先考虑的一些领域的活动……但首先需要介绍一点背景知识。用托洛茨基自己的话来说,自1929年被苏联驱逐出境以来,他一直是一个“不给签证的地球”上的政治流亡者,先后流亡土耳其、法国和挪威,最终得到位于墨西哥的拉萨罗·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领导的左翼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政府的庇护。1937年1月,托洛茨基和妻子娜塔莉亚(Natalia)抵达墨西哥,在斯大林主义恐怖分子的阴影下,他一心想着三个最重要的问题:斯大林组织的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审判旨在消灭所有真实或想象中的反对其政权的人;西班牙内战动荡之际,革命工人阶级的命运;以及在战争再次席卷欧洲之前,托洛茨基发起的第四国际组织的计划的完成。
不足为奇的是,从1936年到1938年,这些问题也成为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主要关注点,即使他们努力争取美国社会党的支持者,加强他们在劳工运动中的影响力,并在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成功工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在这种背景下,坎农和他的同志们,在美国社会党内部活动的同时,还试图为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居留提供便利和保障,并发起一场运动,为“老人”辩护,反对在莫斯科针对他的背信弃义的陷害指控。托洛茨基是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斯大林检察官审判和定罪的,他必须为自己进行缺席辩护,并将莫斯科审判的犯罪性质完整地揭露出来。如果独立调查支持对他的指控,托洛茨基宣布他将自愿向斯大林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刽子手投降。
帕尔默详细介绍了托洛茨基主义知识分子乔治·诺瓦克(George Novack)领导的美国托洛茨基辩护委员会的起源和活动,以及随后由美国著名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主持的莫斯科审判调查委员会。第六章还论述了托洛茨基及其美国追随者揭露斯大林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前左翼反对派安德烈阿斯·宁(Andreas Nin)领导的中派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Marxist Unification, POUM)对西班牙革命的背叛的工作。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向阶级合作主义的“人民阵线”投降的指责,在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与美国和欧洲各种左翼中派主义者之间划出了一条重要的界线——这些团体和个人此前曾表示同情托洛茨基的思想。这种小麦与谷壳的分离对于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至关重要。
这一章最后以两个冗长但有趣的部分结束,它们是关于美国劳工运动的问题:“托洛茨基主义找到了它的海上立足点:坎农及太平洋海员联合会”(Trotskyism Finds its Sea Legs: Cannon and the Maritime Federation of the Pacific)和“生产线上的托洛茨基主义:大生产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的立足点”(Trotskyism on the Line: Footholds in Mass Production and the CIO)。
帕尔默在他的书的重要结语中简单地以“党/国际”(Party/International)为题,回到托洛茨基主义者加入美国社会党的最后几个月,他们被驱逐的情况,以及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立。然后,继续讨论坎农和他的同志们在起草《过渡纲领》和1938年9月在巴黎成立第四国际时发挥的强有力的支持作用。此外,帕尔默的论述强调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美国工人运动中树立了一个与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相抗衡的严肃革命榜样的重要意义,当时来自十一个国家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代表正在巴黎开会,思考他们运动的未来。当表决宣布成立第四国际的问题时,十九名代表投了赞成票,只有三名代表投了反对票,其中包括两名波兰代表,他们的反对基于托洛茨基未来的传记作家伊萨克·多伊彻撰写的一份文件。帕尔默对大多数代表的立场进行了精辟而富有同情心的阐述,并对多伊彻在《流亡的先知》(1963)一书中在这个问题上从未表态的立场则进行了略带倾向性的总结。
帕尔默笔下的吉姆·坎农在投身群众工作时总是最具活力和政治影响力的:1932—1933年在伊利诺伊州的煤田,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1936年加入社会党,在加利福尼亚长期逗留期间加入太平洋海员联合会,当然还有在向群众发表演讲时提出的问题,从赢得罢工和打击法西斯主义,到揭露莫斯科审判,以及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的国际组织。大规模的工作,特别是激进工人的斗争,显然是他的要素和他的灵感。但坎农从未动摇过这样一个信念:只有在这些工作与建设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斗争联系起来的时候,才真正重要。
帕尔默的书对许多与建立这样一个国际党有关的重要主题进行了阐述,其中包括:
●任何推翻资本主义的认真努力——真正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不仅仅是在现有体制内争取一些“进步的”改良——都必须面对的深刻困难;
●根据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模式建立一个革命党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的必要性:一个民主但是高度自律的党,能够在一个共同的革命纲领的基础上整合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有着广泛不同的优缺点;
●需要识别并打击“中派主义”的摇摆不定,这是一种左翼政治,托洛茨基在追随列宁时,将其形容为“言辞上的革命,行动上的机会主义”;
●需要在政治上扩大党的工会工作,不仅仅是倡导普通成员的战斗精神,而是要把革命过渡纲领嵌入到无产阶级最具阶级意识的层面,从而有可能为工人运动打造一个革命领导层;
●需要反对宗派主义,宗派主义不是指积极关注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纯洁性,而是指拒绝接受为找到通向群众的道路所必需的策略。
最后一个主题值得特别关注,因为我们今天可以从坎农的工人党在1936—1937年加入社会党的经历中学到一些东西。帕尔默驳斥了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对所谓“托洛茨基分裂和破坏”的诋毁,他描述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实际上是如何在美国社会党中扮演了一个很大程度上具有建设性的角色,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以及他们是如何在不以任何方式损害他们的革命原则的情况下这样做的。他非常清楚地表明,正是美国社会党的右翼分子和他们的中派主义追随者,通过官僚主义驱逐托洛茨基主义者,引发了分裂,而且他们仅仅是坚持和宣传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关于这个重要的事件,帕尔默写道:
坎农明白这是一种巩固革命先锋力量的策略,因此他坚定不移地决心建立一个具有强大的美国支部的第四国际。这意味着要在阶级斗争领域清除中派主义的残渣和更糟糕的问题,让穆斯特派的倡导者进一步向左,阻止潜在的革命工人漂移到斯大林主义共产党或洛夫斯通的右翼反对派去,甚至解决社会党持续的士气低落,这让坎农的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始终感到不安。一个包容各方的左翼政党的诱惑,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坚持革命和坚持社会民主主义改良主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之间的战略差异,这在历史上一直是一种有吸引力的万灵药。坎农在这一时期的作用,并不像他的批评者经常说的那样,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建设。他尽其所能地看着这种情况发生在社会党内部,意识到从长远看这种前景是不可能的。(第944页。)
怀疑论者可能会指责帕尔默在这里耍了一些花招,因为坎农的目的从来不是拯救已经危机四伏的美国社会党,使其免于进一步衰落,而是为了赢得托洛茨基主义的最佳要素,从而加速建设一个新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尽管如此,帕尔默的评估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进他们的目标时认为有用和建设性的东西,只能被看作是对各种类型的左翼机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的破坏。将托洛茨基主义者斥为“分裂者和破坏者”,一直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纲领核心问题——即革命与改良——的注意力,同时神圣化一种不切实际的“左派团结”,这种团结要求永远不要超越资本主义的界限。帕尔默指出,坎农和他的同志们在美国社会党内部和代表美国社会党的工作,不是鼓动者的工作,而是马克思主义者寻求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推动工人阶级的斗争和觉悟的工作。当然,阶级斗争的发展不可能不产生许多分裂、融合和重组,因为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会出现纲领和战略上的分歧。
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此多的潜在社会主义者已经被建立改良主义的“广泛性左翼”(broad left)政党的响亮号召所诱惑,而其他人似乎满足于充当左翼民族主义,名义上的社会主义政府的强烈支持者(和/或作为“多极化”的反帝国主义传教士),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先驱者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的经验,连同他们在美国社会党和工会的模范工作的经验,值得我们以最严肃的态度加以研究。布莱恩·帕尔默在撰写这本关于坎农的杰出传记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值得所有那些真正目标是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和赢得社会主义世界的人们的感激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