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对杜威哲学的一个评价(摘译)
197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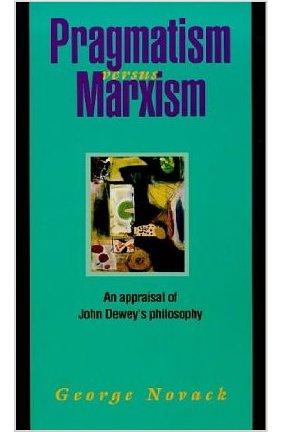
原译:译文发表时标题为《实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作者名字译为“乔治·诺凡克”。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部编辑;商务印书馆1978年4月出版。
说明:本文是译者对诺瓦克《对杜威哲学的一个评价:实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一书的摘译。据译者介绍:“美国纽约拓荒者出版公司1975年出版了托派诺凡克的这本书”。作者“在《导言》中说,他这本书就是根据托洛茨基本人l 940年的建议和要求,经过三十多年之久才写成发表的。”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部编辑;商务印书馆1978年4月出版。
说明:本文是译者对诺瓦克《对杜威哲学的一个评价:实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一书的摘译。据译者介绍:“美国纽约拓荒者出版公司1975年出版了托派诺凡克的这本书”。作者“在《导言》中说,他这本书就是根据托洛茨基本人l 940年的建议和要求,经过三十多年之久才写成发表的。”
实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在实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当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蔓延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搅动了美国时,马克思主义吸引了某些机敏的美国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注意。特别是它的经济学说被芝加哥学派的比较激进的成员当作他们自己在经济、社会学和社会改革方面的著作的辅助性支援来加以欢迎。他们因为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无耻邪恶而看重它,而且因为马克思的历史方法强调环境在形成社会制度和个人特征中是决定性的而对它有好感。
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1906年写道:“再也没有比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更加合乎逻辑的经济理论了”。美国大学中第一个社会学系的缔造者斯莫尔(Allion Small)在他所编辑的《美国社会学杂志》1912年5月号上说:“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主义是最有益的酵素”,他还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将在社会科学中有一个类似于伽利略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
中西部的学者感兴趣的是马克思的分析能阐明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不是马克思的哲学立场或辩证逻辑。在哲学中,他们更重视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的革命结论而不是它的哲学。
杜威是单纯地不关心、而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他在拒绝黑格尔的矛盾逻辑后,感到没有义务同它的唯物主义继承者相妥协。
象凡勃伦、比尔特(Charles A.Beard)、斯莫尔和杜威这样一些在进步党中占领导地位的思想家,都从马克思主义源泉那里借用看来有用于实际目的的任何东西,但是,他们的唯物主义并没有一致之处。虽然杜威参照古代雅典的奴隶贵族政治的作用来说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特殊特征,但他却尽量避免把这同一种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扩展到去发展他自己的逻辑理论。一般地说,进步党思想家们为使唯物主义适合于他们的事物图式和他们思想的习惯,就必定磨灭它的锐利的锋芒,阉割其革命本质。
尽管有政治上的不一致,最早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却对实用主义者答以善意。在早期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西蒙士(A.M.Simons)或象鲍廷(Louis Boudin)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通俗化者的著作中,没有在哲学平面上发生任何冲突的证据。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这个友好地中立的时期,是和进步党人同劳工站在一起反对财阀政治相一致的。这种亲睦一直坚持到三十年代初期,随后让位于不信任,最终酿成公开的敌对。
这个变化的后面有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世界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上支持者的削弱。另一个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胜利,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出现。随着工人阶级作为最大的革命力量来到前列,它的学说和方法就越来越同一切其它的学说和方法尖锐地相对立,并遭到越来越强烈的攻击。
这种发展也影响了这个国家中实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从反对墨守成规的保守主义中的一个同盟者,变成了对自由主义的最珍爱的思想和基本立场的一个威胁。尽管有把这种倾向调和与结合起来的微不足道的努力,主要的实用主义者却越来越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含意相敌对。同时,少数真正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受了俄国革命领导者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鼓舞,也帮助了划分敌对的哲学派别的工作。
这种相互排斥,又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帝国主义对于美国思想生活的日益增长的干与(预),以及在它的压力下实用主义的屈从,而进一步凝固起来。主要的实用主义者采取了一种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保卫者的无保留的立场,不仅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赝品,而且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代表。
到了三十年代,杜威感到已经没有好好熟悉马克思思想的欲求了。资本主义危机和马克思主义随之而来的蔓延,使得他知识中的这个缺陷不那么可怕了。他利用其作为对莫斯科审判的调查委员会主席的工作〔机会〕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它的最后判决是说马克思的学说无可救药的沾染了黑格尔主义,并导致适合于神学的绝对主义。只有恢复对于工具主义的优点的信仰,致力于保卫和扩展一种超越于阶级斗争舞台之上的民主政治,文明和文化才能得到促进。
马克思主义对实用主义的态度
在一部分具有学院背景的激进知识分子中间,曾经流行过关于杜威主义的优点以及它同马克思主义是可以相容的幻想。这些社会主义运动的同路人曾在有关这两者的真实关系的问题上制造了相当大的混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主义运动右翼的思想家首先企图使马克思主义同实用主义配合起来。在《社会主义的较大的方面》(1913年)一书中,瓦林(w.Engtish Walling)从杜威那里汲取其教育、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许多思想,并力图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实用主义流派在大西洋彼岸产生前的实用主义者。
在后来的调和者中间最著名的是若干自夸是“非独断的”思想家的哲学教授。这使他们能够断定,实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即使不是同一的,至少也是在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上彼此和谐一致的。杜威的两个学生在这个范围内有着惊人的意见一致。一个是拉蒙特(Corliss Lamont),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哲学;另一个是胡克(Sidney Hook),纽约大学的退休哲学教授,他在1940年以前曾醉心于左翼政治,以后又经历了一个作为美国国务院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辩护者的生涯并在1972年支持尼克松。
在1947年2月25日《新群众》杂志上辩论这个问题时,拉蒙特写道:“我认为无可争辩的是杜威的庞大的哲学体系,其主要含意和内容是彻底地反唯心主义的,而且是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总的世界观相一致的力。胡克则在1940年出版的《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一书中断言:“在今天,表现了马克思思想的最好的要素的、世界上最卓越的人物是约翰·杜威……他是独立地发展和系统地阐明了这些思想,而这些在马克思那里是没有的。”
费攸尔(Lewis Feuer)支持这个判断。“在比尔特、凡勃伦和杜威这些人那里,古典的美国社会科学不仅受马克思的影响,而且和马克思有着相同的基本原理。这些美国人对于下层普通人的信任,也是基督的社会主义的信任;他们认为科学是解放的方法,这种信心和他们认为经济因素在人类历史中具有首要性的这种信念,是象马克思的信心和信念一样有力的。古典的美国社会科学家在他们注视其社会界的方式方面,确实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许多学者发现一种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演进,而这是三十年代的自然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政治、哲学著作》导言,第9一10页)。
在纯意识形态方面,把这两种哲学捏在一起的这种企图,或者表示重新陷入美国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幼稚状态,或者表示没有能力再越雷池一步。但在拉蒙特和胡克那里,这种等同却执行着一种较为确定的功能。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都避免同任何左翼政党或纲领在最终发生什么关系。他们寻找着减弱资本主义统治者和工人群众之间利益冲突的道路,或者寻找把这两者调和起来的某个共同领域。在探索这种妥协时,他们在理论上的出发点是否认这些阶级各自的世界观之间的根本区别。拉蒙特在人道主义的名义下,而胡克则在一个荒瘠和卑屈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做这件事情。
为维持这种错误立场,他们不仅违背明显的事实,而且无视相敌对的哲学的最权威的声音。杜威本人是注意到工具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的对立的。罗素说杜威把辩证唯物主义和神学等同起来:“我有一次听他说,在艰难地从传统的正统神学中解放出来之后,他不打算让自己被另一种神学所束缚住”(《西方哲学史》第848页)。杜威倾向于把任何类型的系统思想都分类为“绝对主义”、“独断主义”或“神学”。在任何场合下,他都精明地和充分坦率地坚持他自己的观点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
从普列汉诺夫经过列宁到托洛茨基的一切关心这个问题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都把实用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尖锐地区别开来。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六章第四节)中,列宁指出实用主义如何象实证主义一样,归根到底是从同样的主观主义前提出发并达到同样的反唯物主义结论。
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科学理论,不可避免地要同作为中间阶层的先入之见的表现,作为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工具而发挥作用的杜威主义发生冲突。它们之间的深刻对立,已经通过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这些倾向之间冲突的爆发表现出来。在美国,冲淡或抹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的每一个企图,都或迟或早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思想同实用主义的目的和思想联结起来,或甚至在一开始就明确地用杜威主义去补辩证唯物主义之不足。例如,伊斯特曼(Max Eastman)就是如此。他在三十年代末期抛弃社会主义之前,就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吸收进工具主义,并把列宁描写成在实际上是杜威的一个没有公开宣布的门徒。
美国哲学中的阶级表现
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互关系的记录,它们的主要代表的证词,在它们的阶级联结中的歧异,它们的方法和主要原则应用于特定场合时的冲突,这一切都有助于证明两者的根本对立。它们所具有的无论什么的共同点,都是附属于它们的主要的不一致的。这两种哲学并不是和谐的与调和的,而是在基本上互不相容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
它们表现了具有相互对立的利益和愿望的两种不同社会力量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道路上的战斗意识形态,实用主义则是走向衰落的中间阶层力图抓住任何救命手段的安抚性哲学工具。
在今天的美国发生着作用的主要社会倾向,具有三条主要的理论路线。具有反动、军国主义和镇压的倾向的垄断资本主义,赞助最落后的偏见和从宗教到种族主义的古老思想,它力图把它的掠夺目的隐藏在保卫“民主”的口号后面。当“自由世界”的旗手们自己领头走向蒙昧主义和文化上的倒退时,就乞求封锁或甚至消除进步的社会、政治和哲学思想。
这并不是同第二种倾向工具主义气味相投的地域。工具主义在尖锐的区别被弄得模糊、轮廓含混和事物的准确位置不确定的朦胧世界里,才感到最安适。当它能够避免在尖锐的两种选择中作出抉择,和能够磨平与掩饰歧异时,它就畅快。它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在主要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它靠含糊和杂凑过日子。
第三种倾向马克思主义,不能容忍蒙混和权宜之计。它诚实和老实地断言资本和劳动的利益是不相容的,它们的斗争必将进行到底。这种关于二十世纪“压制不住的冲突”论,对于实用主义自由主义者来说,听起来就象疯子的叫喊或世界末日的霹雳。
实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异同
〔第一,关于辩证法〕
杜威把辩证法和黑格尔的思辨方法等同起来。
杜威主要从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版本上去了解辩证法。在他看来,在客观事实中看到在运转着的矛盾的逻辑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一种把互不相容的对立结合在一起的荒谬事情。
尽管杜威拒绝这些名词所代表的东西,他在《经验和自然》一书中的分析,却包含有对实在的辩证法的和唯物主义的观点的要素,但这些却被表现在一种没有展开的和偶然的形式之中,并被蕴藏在一种相反的概念的模型之中了。
〔第二,关于矛盾观〕
当杜威走向工具主义时,他用一种特有的方式修改了黑格尔逻辑的范畴。他用他自己的倾斜性的、渐进主义的“冲突观”,去代替黑格尔关于矛盾的界限明确的定义。在个别情况下敌对各方之间的斗争,就其本性来说,并不必然导致一方把另一方毁灭的否定。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之间的“不平衡”,是在一个改造了的情况中,由差异的调整和调和来加以解决的。据此他就在其逻辑中删去了辩证法的主要之点,使它围绕着改善“麻烦情境”、而不是围绕革命化而旋转。
以奴隶主叛乱告终的1820-1860年期间的妥协,证明了杜威的逻辑只适用于这样一些情境:在那里,敌对社会力量之间的对立,还是如此地没有展开,以致能通过相互顺应来予以仲裁,但当它们的分歧达到破裂点时,这种方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就垮了。它只适用于阶级斗争还未达到最大限度的紧张的时期。
而另一方面,符合于阶级斗争的真正动力学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却能说明其挨次相继的一切阶段,从相对的阶级和谐与妥协盛行的进化时期,一直到公开的阶级战争提上议事日程的革命的爆发。
杜威认为矛盾只有主观的特性。它们存在于头脑中而不存在于外部世界。他的门徒胡克激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他说,虽然判断、断言和证明能够是矛盾的,但把矛盾归诸事物和现象,却是无稽之谈。“自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以来,矛盾的是命题或判断或陈述,而不是事物或事件,这已是逻辑理论的常识了”(《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第202页)。
关于矛盾的本质和范围,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比形式主义、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学派的概念要广阔得多、正确得多的概念。矛盾不仅客观地存在着而且普遍地运转着,因为每一事物由于它的内在本质以及其外部联系的必然性而运动和变化着。
杜威确实试图通过把肯定和否定同物理、生物过程联结起来,超越其功能主义而达到矛盾性的客观性。他说自然界的结合和分离,动物中间的选拔和排除,就是逻辑理论中肯定和否定的原型。
在物理的、有机的和智力的平面上有着可以比较的过程,看来就指出了矛盾性的普遍性。然而,杜威却无意于采用这样勇敢的一个概括。
〔第三,关于认识论〕
辩证思想家能够同意杜威认为没有一劳永逸地确定的绝对真理的观点。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但是,杜威把永恒真理的不可能性同不存在客观真理相混淆了。
杜威在反对某些唯心主义者时所说,真理并不现成地传给我们,而是人的历史活动和连续不断的实验的产物的议论,是可以接受的。对真理的探究和对错误的揭露与根除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然而,杜威甚至没有对真理的相对方面作一正确的解释。
象辩证法家一样,杜威承认一切事物永远不断地走向灭亡。他从认识到这个事实滑到一种没有为绝对真理留有余地的过于简单的相对主义。
〔第四,关于伦理学〕
杜威的抛弃不朽的原则,以及他的关于道德是和有效的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概念,是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所同意的。
然而,杜威的伦理观的主要议论同马克思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教导相冲突。在道德冲突和阶级冲突的关系上他们根本不一致。他鼓吹一种为一切人所共有的无阶级性道德,而且在改善或解决冲突中和稀泥,他否认道德标准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有阶级性。
〔第五,关于民主观〕
〔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哲学在民主问题上相抵触。在原则上双方都致力于民主目的。但它们在对这整个问题的看法上却不一致。民主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上?在现在的条件下如何能保持和扩大它?我们社会中哪些力量是它的保护者和促进者?马克思主义用一种方式回答这些问题,杜威主义用另一种。
自由主义者拒不承认下列事实的意义,即民主之进入历史,包括进入美国史,并不是用一种和平的逐步的方式,而是通过革命。就自由主义者认识到这个事实而言,他们也把它当作偶然的和无关的事而加以排除。
反之,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民主是阶级斗争的政治产物。
美国哲学的一条新路
美国哲学面临20世纪世界的整个发展形势,要找一条使自己同劳工主人结盟的道路,否则就毫无结果,但这只是情况的一个方面。工人运动本身也需要有一种科学的哲学来启蒙和指导,以便克服它现在的困难。
美国哲学和美国劳工一道,现在来到了十字路口。它不能使时代继续停留在实用主义阶段。如果它要避免停滞不前和倒退,它就必须找到一条新路。
激进人士经常谈到把马克思主义美国化的需要。这个工作必须通过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和思想应用于美国在一切领域中的发展的问题来实现。
在哲学中,这一工作不能不通过对工具主义的彻底的批判性评价来进行。因为作为美国思想中最进步的学派,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前驱,必须要以一种辩证的方式来慎重考虑杜威主义,说明它已经过时,也说明它的优点和积极成就。
从根本上说,实用主义是和辩证唯物主义不相容的。它们的方法和学说是不能调和的。决不能使革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自由主义改良派的意识形态混杂起来。在这两种对立的世界观中作出抉择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对一切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哲学,而且也要对小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宣战到底,而实用主义在其一切基本的方面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精髓。
而同时,又不能把实用主义斥责为完全错误的、没有价值的和要一古脑儿抛开的。它并不是中间阶层的思想代表偷偷地加诸于这个国家的哲学上的。它产生于深深植根在美国人民历史和习惯的那些倾向之中。象资产阶级民主本身一样,在美国的观点和制度的发展成长中,它是一个在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阶段。
作为反映美国社会发展的进步的和不成熟的以及倒退的趋向的混合物,在它的错误和结构上的不适当中间,包含有大量的正确的和有价值的见识。实用主义在削弱教权主义的权柄、摆脱传统唯心主义和学院理性主义的最坏弊病、提出科学实践是认识的模型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帮助曾经是远离人民的专业人员的领域的哲学同日常生活的需要发生密切的交流。它竭力把哲学带到尘世来,使它朝着解决美国人民的社会问题前进。
工具主义的知识分子在表述平民的要求时,抓住了美国生活中的某些最健全的倾向。杜威主义给予技术的崇高地位,它的对于为增进人的社会力量和共同财富而征服自然的价值的强调;它的关于实践在人类生活和思维中的首要性的重视;它的坚持通过把思想付诸实际结果的检验来确定其真理性和价值;它的在其最勇敢代表那里接近于唯物主义的功利主义;它的进化的乐观主义;它的藐视任何的绝对化;它的民主主义;它的要求哲学参与社会改良,工具主义的这一切贡献都是美国思想的永久收获。
当然,在这各点中没有一点是为马克思主义所不熟悉的。科学社会主义或者已经把它们吸收到它的世界观中,或者能容易地同化它们,以及在事实上给予它们以更有根据的表述。
这样,尽管工具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它却有某些因素和倾向能够提供一条通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的确,工具主义在其发展的界限内,趋向于否定它本身并寻求一个在左边同马克思主义的联盟。这惹得象胡克和拉蒙特那样的某些把事情搞错了的知识分子,把这两者混淆和等同起来,或甚至把辩证唯物主义从属于杜威主义。
工具主义的固有的激进主义,要求一般观念在社会实践中证明其效力。然而,这个要求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受科学指导的革命运动才能充分实现。这样,在某些情况下,实用主义者就有可能通过一个内在的革命,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正如工人运动的先进部分,能够通过他们自己经验的教训,打破传统的经验主义而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至于他们对新信念坚持得怎么样,那是另一回事。
在使哲学成为人民的向导中,将附带地第一次实现实用主义本身所提出的希望。杜威曾试图使哲学走出图书馆和课堂,并使之成为比较好的教育的一个工具,启发人民的工具,改革我们的社会关系的工具。这个进步的目的属于我国智力活动的最好的传统之列。马克思主义将建立在这个希望上面。
但杜威的世界观却使他探索着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力量中间去实现这一工作。
(徐崇温 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