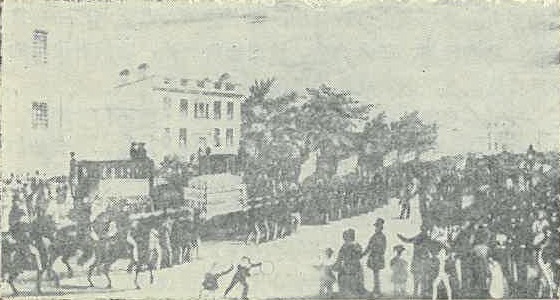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阿萨·勃里格斯《马克思在伦敦》(1982)
2 马克思所见的伦敦
当1849年马克思来到伦敦的时候,伦敦已经是一个拥有250万人口的大城市,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一片很大的建筑区,从西边的富勒姆伸延到东边的滨河镇波普拉,长达九英里;从北部的海伯里连贯南部的坎伯威尔,长达七英里。
当时,伦敦大体上还是一个乔治式风格的城市,它的地区包括伦敦的若干古城(现在的伦敦城)、威斯敏斯特、布卢姆斯伯里、梅费尔、玛丽勒邦、荷尔本、依斯林顿、肖尔迪契、贝思纳尔—格林、波奥和南瓦克,这些地区无论在社会结构和外表上都有很大的差别。此外,当时伦敦各区的界限要比19世纪后期划分得清楚,虽然远在19世纪20年代,一位激进的作家威廉·科贝特就已经把它谑称为“大赘瘤”或“坏透的”赘瘤*。
*科贝特指的是伦敦的建筑有损自然风光,就象人体上长了赘瘤那样不雅观。——译者
还有一位激进的出版家G.W.M.雷诺在1846年开始出版他那套写得非常成功的书《伦敦的奥秘》。在该书的那篇非同凡响的序言里,他既谈到伦敦的“无限壮丽”,又谈到它的“可怕对照”。“数以千计的塔尖,层层叠叠,高耸云霄”。然而“无穷无尽的财富”却与“骇人听闻的贫困”相匹配,而“极尽奢华”却须由“饱受赤贫”来加以衬托。
在伦敦这个“大赘瘤”里,最重要的地区是在泰晤士河北岸。全国的金融中心,其中包括英格兰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就在伦敦城内。泰晤士河北部同时也是文化、商业和行政中心的所在地,白厅、议会、法院以及皇宫,都在这个地区。不过,在河的南岸也还有一些重要的公共场所,其中包括肯宁顿公地和再远一些的克拉彭公地;这里还有兰贝思宫,这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伦敦的住所。
在1849年以前,伦敦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经历过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当时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工业规模和产量都有所增长,而伦敦的工业却已经走下坡路了。例如,斯比塔菲尔德兹的老式丝织工业,由于“条件恶劣”和失业严重,当时已经成为一种令人伤脑筋的工业了。尽管如此,当时伦敦的一些重要工业活动仍然保留着,而且确实还有所扩展,其中包括印刷业、机器制造业和消费品制造业(诸如火柴、服装、啤酒和肥皂等)。同时,跟拥有大量工厂、高炉以及新兴工业城镇的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对比之下,伦敦比较缺乏一种“阶级”意识,但它却拥有高度组织的伦敦各“行业工会”,这是一个个工人集体联合组织起来的集团,当时以制鞋工人的人数最多,裁缝工人次之,其中一些组织具有激进的传统。
最后,如果从伦敦变化的速度来看,建筑业是一项主要活动,这个行业同样也促进了工人协会的建立。甚至在维多利亚女皇登位之前,伦敦就已经有许多大规模建设的方案——街道、码头以及后来的铁路和地道。可是,当时伦敦的新的地下管道系统这一巨大的工程,还没有开始动工。当马克思来到伦敦的时候,伦敦已经有意地被排除在1848年颁布的英国第一个全国公共卫生法令的条例之外*。当时,泰晤士河河堤的工程也还没有动工。
*这是由于当时人们考虑到伦敦的公共卫生的问题很大,需要专门的立法来解决。——译者
房屋的修建经过几起几落,其间19世纪20年代在跟伦敦毗邻的西部地区曾兴旺一时,它的发展席卷到附近的村庄,如帕丁顿等。有一个叫做蒂本尼亚的地名,源自于蒂本树(即现在的大理石门所在地),从那时候起便消失了。当时该地名所指的地区包括帕丁顿、贝斯沃特、诺丁希尔和北肯辛顿。另一个地区,即贝尔格拉维亚,在19世纪50年代延伸到切尔西、皮姆尼柯以至到维多利亚(虽然以维多利亚女皇命名的火车站——通向欧洲大陆的门槛,直到1860年开始使用)。
当马克思来到伦敦的时候,对于许多伦敦人来说,要从伦敦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是很不容易的,而且除了步行以外,也很不便宜。
第一个地铁站直到1863年才开放,至于公共马车,当时尽管已经流行起来,但毕竟多少还是新鲜玩意儿。最早的两部公共马车(每部由三匹马牵引),是在1829年由乔治·施里比亚引进的。乔治·施里比亚是一个在英国出生的马车制造者,在巴黎住过。这两辆马车从帕丁顿—格林出发,沿着新开路(现在的玛丽勒邦和厄斯顿路),经过安琪儿、依斯林顿,直到英格兰银行,作定时往返。到1849年,这样的马车已经有620辆。当时已经有可能花1个便士从查林十字路乘到坎登镇,而有许多路段的车费是3个便士。只是到了1856年伦敦通用公共车辆公司成立的时候,那些仅在有利可图的路线上招徕顾客的小车主,才让位给提供公共服务的大车队的老板。
水路交通也持续不断,装载量为125名乘客的轮船,从早8点至晚9点,全日往返于伦敦桥和威斯敏斯特之间。尽管如此,一些商人、律师、秘书,尤其是货栈人员和手工业者,仍是安步当车。当时,伦敦城依然保留它的兼作生活区和工作区的特色,可是不久以后,它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却成为“鬼市”,因为成千上万的职工都回到市郊去了。
在维多利亚女皇登位之前,铁路已经通车了。由德特福到伦敦这条线路在1836年就已完工。艾斯顿车站在1837年落成,滑铁卢车站在1848年落成(国王十字路车站也接着在1852年落成)。铁路给城市的面貌和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变化,比其他任何革新所起的作用要大,虽然铁路的作用是错综复杂的,并且是有争议的。铁路引起巨额的投资,带来了就业,但也导致投机活动的猖獗,新货栈和车站的修建,旧房屋的大规模拆除。最后,铁路还导致比较民主化的旅行方式的出现,但也引起新的社会和物质差异的产生,即所谓“轨道两边”*;铁路促使货物的大规模运转,使许多货物的价格便宜起来,但同时也引起奢侈品的泛滥,同样重要的是,铁路还导致一种新的时间观念的确立。铁路是跟定时和准点联系在一起的(《布莱德肖》这本铁路时刻表最初出现在1839年),但同时令人更为烦恼的是,它又跟一种更快的生活节奏和必不可免的事故联系在一起。
*指富人住在一边,穷人住在另一边。——译者。
狄更斯的《董贝父子》(1848)一书,如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有不少精彩的段落是描写铁路的。他对铁路的看法是:既是进步的象征,又是死亡的工具。
1846年是建设新线的高峰年,到1848年已完成了不少。作为1848年欧洲革命背景的1847年财政崩溃,其原因往往被人归结为铁路的投机买卖。
至于从国内其他地方向伦敦移民,则早在铁路修建之前已经开始了。其中有十年时间,来自英国国内和国外的移民激增,马克思本人就是这些移民中的一个。的确,根据人口普查,从1841到1851这十年间,大约有33万新居民来到伦敦。他们的经历很不相同,财产的悬殊也非常大。少数人通过做生意或各种关系发了财,而大多数人则沦为手工业者或仆从,这种“楼上楼下”的强烈对照现象,一直持续到维多利亚女皇统治的后期。一些迁入伦敦的人,他们的状况是每况愈下,而不是步步高升。从1853—1900年,随着铁路和地铁的扩建,不下12万人搬迁了。贫民虽然经常要搬来搬去,然而他们从来也没有消失过。《泰晤士报》在1861年写道:“贫民只不过是挪了个地方,而并没有消失。”
早在19世纪40年代,伦敦的不同地区的建筑密度就已呈现鲜明的对比。“过于拥挤”这个词首先是在19世纪40年代使用起来的。此外,一些社会统计学家兴致勃勃地把这些差异跟其他社会指标——诸如疾病和犯罪等——联系起来考察。当时已经有一个由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组成的教育网,然而,由公共基金拨款的普及教育制度直到1870年后才出现。
与此同时,公共卫生的设施,诸如住宅条件等,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用近代的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伦敦“活像一块肮脏的海绵,一个满布污水池和水井的蜂窝,水源供应来自于作为污水排除口的河流,疫病跟贫民窟结了不解之缘,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接连不断地流行的霍乱”。霍乱是在1831年第一次“光顾”伦敦,再一次是在1849年,也就是马克思来的那年。然而在后果上比霍乱更为严重的是像斑疹伤寒这种不那么引人注意的疾病。当时伦敦的最高死亡率发生在荷尔本、肖尔迪契和贝思纳尔—格林这样一些比较贫困的老区,这个事实并不是偶然的。尽管当时伦敦被誉为比大多数欧洲城市卫生,而且“卫生思想”比社会主义思想所拥有的信徒还要多,但这也并没有任何值得自慰的地方。

霍乱国王的宫廷:《笨拙》杂志在1852年发表的一幅刻画伦敦贫民窟卫生条件的漫画
1855年,也就是在马克思来了六年以后,才成立了市政工程局。该局立即着手去设计“一个下水道系统,以防止市内任何一部分下水道通向泰晤士河在本市或邻近本市的河段”。接着,它又把注意力放在扩建旧街道和修建新街道上,放在修建泰晤士河河堤和检查煤气供应系统上。至于拆除贫民窟,与其说是以上改进卫生环境的规划的首要目标,倒不如说是它们的副产品,然而此举还是产生了惊人的社会影响。在这以后,伦敦的社会阶级分野更为明显,出现了专为某一个阶级修建的街道,这可以说是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伦敦的一种特色。
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郊区发展得最快的是坎伯威尔。从1837年到1901年间,它的居民人口增长了七倍。这个区里住的是那些受尊敬的人,其中有人数日益增长的职员,这些人在劳动力更替过程中形成一种日益重要的因素。这里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有很多好房子,但在以后几十年间房屋的标准趋于固定和划一,终于使坎伯威尔成为在一片片台地上建筑了整齐划一的两层砖房的地方。
在19世纪后期,伦敦在英国社会主义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不过,在19世纪30—40年代,特别是在宪章运动早期,它在这方面看来是落后于工业的北方。在大宪章于1838年5月颁布以后,主要是外省的宪章派组织起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去争取他们的著名的“六点要求”——普选权,秘密投票,年度议会,议员领取薪俸,取消对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取消腐败的选区。
受马克思影响的社会主义领袖亨·迈·海德门曾写道:“宪章运动领袖所犯的最糟的错误是忽视了伦敦,等到他们醒悟的时候已为时过晚”。海德门这个在宪章运动过了很久以后所作的估计,未免有些夸大,因为尽管伦敦在宪章运动史的开头即1838—1839年期间相对来说不够活跃,然而它始终是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主要中心,并在1848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831年在伦敦成立了工人阶级全国联合会,在这前后还举行过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例如1833年在科德巴斯——菲尔德所举行的集会。当时在林肯旅店和坦普尔一带,得到公众大力支持的激进书店林立,这些书店无视报刊税例,传播一种漏税的报刊《穷人卫报》。
1836年6月,在工人阶级有智慧有影响的那部分人的领袖的倡导下,成立了伦敦工人协会,接着在1837年成立了更富有战斗力的东伦敦民主协会。然而,直到1848年,伦敦才成为宪章运动的中心。在这一年,伦敦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包括“老行业”的工人,都投入了宪章运动,从而在伦敦的宪章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活跃的革命分子,其中一些最积极的宪章运动分子日益趋向于接受社会主义纲领。宪章运动的激情甚至在1848年后仍方兴未艾。《伦敦劳动者与伦敦贫民》(1851)一书的作者亨利·梅休曾写道:“手工业者几乎人人都成为欢迎激烈的政治见解的赤色狂热无产者”。
当1848年革命席卷欧洲的时候,在伦敦当时情况下,有以下四个因素使革命力量受到遏制:
第一、拥有财产的伦敦中产阶级力量雄厚,他们在关键时刻起来维护法律和秩序。
第二、许多激进派并不是革命者,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特别不愿意使用武力。
第三、伦敦工人的收入比外省工人要高。这个事实无论对于分析1838年的形势(当时宪章派在首都的力量比外省强大),还是十年以后的形勢(当时首都存在明显的不景气和严重的失业现象),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组织良好的市警部队有一种行之有效的非武装控制办法。这支部队成立于1829年,它能够通过暗探和告密者打入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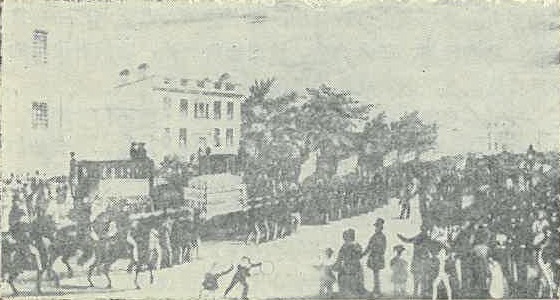
1842年群众向下院递交宪运动请愿书的盛况
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在泰晤士河南岸的肯宁顿公地举行了一次很有名的群众集会,当时他们想到议会去递交请愿书,而这时候维护法律和秩序的部队却作好充分的准备。威灵顿公爵,也就是滑铁卢战役的那位英雄,已在卓有成效地指挥这支部队。他调动最精锐的队伍把守住泰晤士河上的布拉克弗赖厄斯桥——宪章派预定的渡河点。那次一共出动了400名市警,其中有40名骑士。

1848年在肯宁顿公地举行的宪章派群众集会
(此幅珍贵图片是经英国女皇陛下批准复制的——作者)
伦敦有组织的劳工的早期集会地点,原先都在一些靠近工人阶级住宅区的地方,例如伊斯林顿的哥本哈根—格林。但这主要是1848年左右的情况,当时海德公园和特拉法格广场对于大多数示威者来说是太远了,在那些地方闹事是后代的事情。
在肯宁顿公地集会以后,伦敦的革命危险并不来自公开集会,而来自秘密聚会。马克思没有在革命前夕来到伦敦,而我们知道,在1848年出现大骚动以后,接着就连经过改良的运动也都不断发生分裂、瓦解以至自行消失,而不是被武力镇压下去。马克思在伦敦度过他的后半生的34个年头,而在1850年以后,他在大部分时间内感受更多的也许是伦敦的财富和力量,而不是它的革命潜力。在1847年财政危机和1848年的失业、饥馑以后,又出现了繁荣。恩格斯后来就1850年末的情况写道:“任何一个有眼睛并且准备用眼睛来看东西的人,都只能认为革命的浪潮在平静下来”。
在肯宁顿公地集会后不到三年,大群人又涌向伦敦,但这次他们不是去举行政治示威,而是去安安静静地观览国际大博览会,它在海德公园新修建的水晶宫中举行。在那时候,人们对工业成就所产生的自豪感,压倒了对社会崩溃的恐惧感。的确,像19世纪40年代那样活跃的工人阶级政治活动,只是过了一代人以后,即在19世纪80年代期间,才又重新出现。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