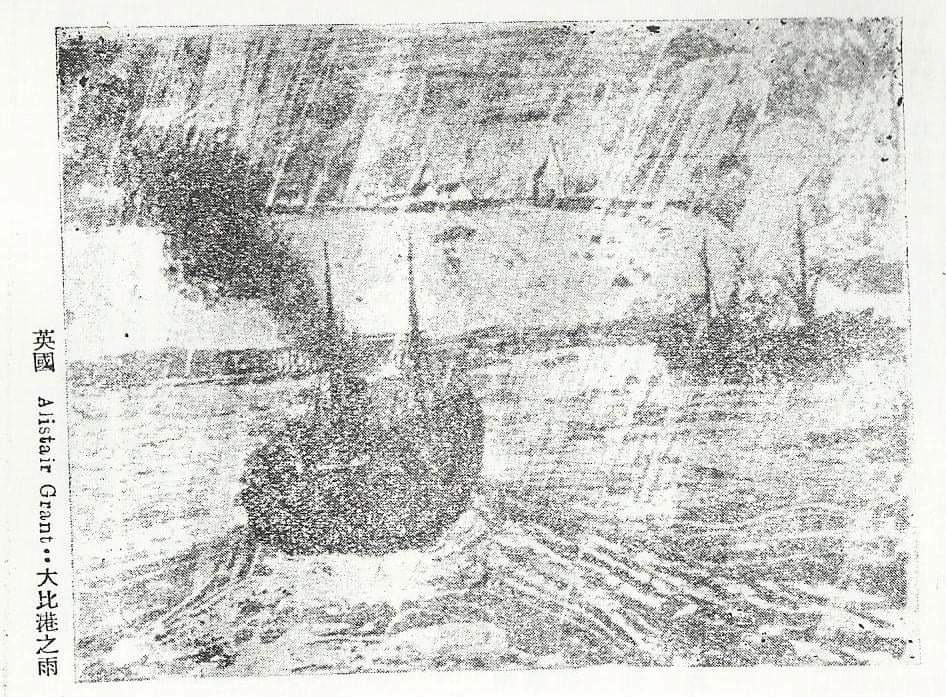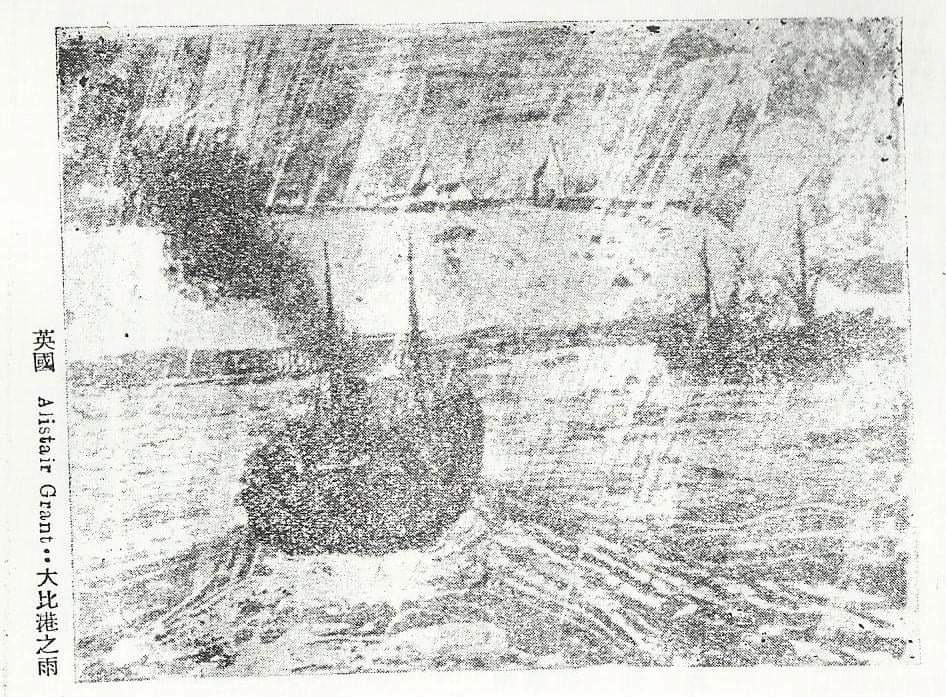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工人小说 相关链接:波臣《回顾》(1918—1948)
〔小说〕
风
〔说明〕刊载于香港《文艺新潮》第1卷第12期,环球出版社1957年8月1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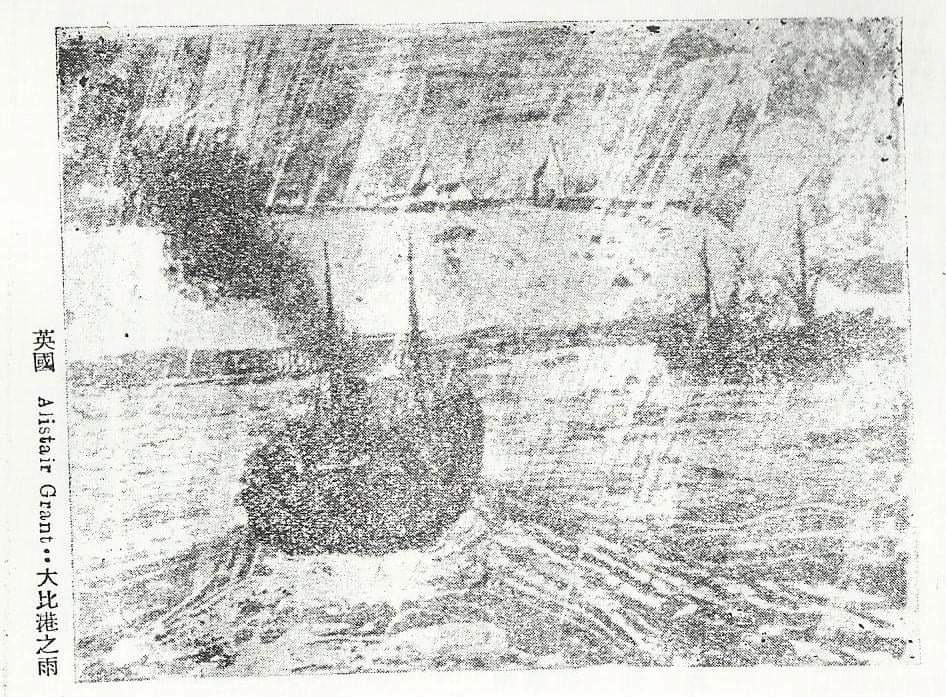
五点半钟,刚开过了晚饭,我们的“头”——浑号“癞痢头”——就在喊了:
“阿房,把麻将桌子摆下!”
我洗清碗盘之后,赶着去做了这桩要事,在后尾蓬布下安好了桌子和座位,麻将牌也提来了,癞痢头首先坐下,跟着叫我去给他喊“搭子”,人手齐了,我忙了一会拿烟,开啤酒。偶尔向远处一望,火红的太阳已经粘在海皮上,一会儿化成了指头大的一条小金鱼,吱溜的往深水里钻下去。一丝丝的风掠过来,有了点凉意,不再是白天的热风了。癞痢头的牌风也顺,他喊着:
“碰,单钓东风,辣子!”
在他推倒牌的时候,风更大了些,好像风是被他喊来的。他的酒糟鼻子和永远瘪着的薄片唇,都点上了点笑意,后来竟然笑得露出了那口黄牙:这样笑,是他和外国人讲话的时候常看得到的。这回,自然是那张东风引起的,这阵凉风也助了把劲,他一面笑,一面说:
“好凉风!年头可是改了,二十年前,船到这里,黑夜白日,哪有这么好的风!”
“出了名的红海,蒸锅似的蒸死人!”对门的三级慨叹着往事。
“年头还是那年头,红海还是那红海,改的是外国人的船。”站在旁边的富老头顶了一句。
“老头,你怎么还爱抬杆呢?船改在哪里?船改了,天气就变了?”癞痢头歪起了头,瞪了富老头一眼。
“我哪一点抬杆?想想看:二十年前的船跑几哩?顶多是五六哩,现在这只可下过十六哩?差到哪里去?风是船快带起来的!不信,住了车,试试看!”
“什么都没改,就是我的脾气改了!”癞痢头又瘪起了嘴唇,从牙缝里,鼻孔里往外哼气,手上加劲摔牌!
“我的脾气也改了!”富老头愤愤的转身走了。
我知道癞痢头还要骂些不三不四的话,不愿听下去,也赶快闪开了。我从右边过道走向第五舱,这儿没有后座的房间紧遮着,风更大些。刚从灯影下出来,虽然天上还抹着晚霞,海水亮堂堂的闪着回光,可是眼前却有点黑糊,我挨着一个人在舱盖上坐下来,等到眼睛变过来,才看清了这人就是富老头。
“癞痢头的脾气真是改了,”富老头叹息地说:“要是二十年前,你可真伺候不了他,阿房!”
“怎么会伺候不了?”我问。
“他是有名的屠户、刽子手!”
“嗯!”我吃了一大惊。
“我和他干过一场好的,也就是我!”
接着,富老头给我讲了以下的故事。
※ ※ ※
二十年前,就在这地球上的蒸锅里,有两只货船,一先一后的航着,两只船的样式相同,大小也都在五千吨上下,时速呢,从船头激起的浪花看,都不过六哩,要是往上看,看烟囱里冒出的烟。都轻袅袅的不带劲,倒像就会住车哩!说到烟囱,两只一色的粉蓝色,正表明了原是一个公司属下的姊妹船。
海水是平静的,像新瞒成的一面鼓,鼓面绷得紧紧的,要把两只船当鼓槌一样的弹起来。时当正午,天上白茫茫的没有云,天蓝浅得有点发白。稍远一点的山便消逝在光和热交炽着的大气圈里,一点阴影都不显。近旁的山,闪闪烁烁像是无数的钻石在发光,有时联成一道电弧光,灼射人的眼睛。山的背阴面,却又一片墨黑,黑得像浓夜一般。
要是当水手,在甲板上敲敲铁锈,抹抹油漆,也不过是试不着风,衣服叫汗水湿透着,眼睛像是蒸气嘘着,山呵,水呵,不像真的,倒像在梦里梦着的一般,有些飘忽忽的。不过如此!要是在火舱里干烧火,那,可就尝到点货真价实的蒸锅味了!
两只船的火舱间打造得一样,燃料也是一样的煤,只是烧火的讲话的口调不同。
后面那船的烧火佬正打开火门,送了两铲煤进去,关了火门,柱着煤铲在擦眉梢上的汗。两个打扇仔左右开弓的站在他的两旁,两膀用上十分力地往他身上扇着。打扇仔为了自己也沾点对方的风,不能不下这么大的力。可是风和蒸气差不多,比火苗凉些!
“头手”由通引擎间的小门钻过来,在烧火佬的背后发了话:
“阿兰姆,你唔好尽乘凉,至紧添煤先,水汀唔够——”
“丢你个老母!你来添!”烧火佬一转身把煤铲扔了过去,鼓着眼睛说。
“唔好呢样,我的烧火佬有打扇仔相帮,都烧唔起水汀,航不过呢上海佬格船,我哋没饭食啦,呢条船系最后一条归我广东佬做,要系做不过上海佬,返香港,只好另觅嘢食!”
“我丢个上海佬!”烧火佬听了头手的哀吿,口里咒骂着上海佬,哈腰去拾起了那煤铲。
就在这同时,前头这船的升火阿根,也正加了两铲煤,关了火门,拄着煤铲,用手指滤着额头上的汗水,可没有人给他打扇,他的眼已被汗湿透,腿也东溜西荡的,他摸索着出口的梯子,想爬上去透口气,刚上了两步,头脑癞痢头正从引擎间里过来,手里握着一根粗藤条,一下子打在阿根的背上,随口骂着:
“娘个拆必!”
阿根嗳了一声,向后翻下来,几乎压上癞痢头,癞痢头一闪,他倒在花铁板上,癞痢头又狠狠的在他身上抽了几下,踢了几脚,阿根却一声不响了。
三班的升火和拿煤的来接班了,癞痢头叫他们把阿根抬到上面甲板去,开开救火龙头,冲了一回,阿根才醒了转来。
十二点,下班的人到船尾吃中饭,经过阿根这里时,虽然也瞥了一眼,可没有人哼一声。这值不得惊怪,谁也替不了谁。阿根湿淋淋的晃悠着到了后尾,倚了墙,坐在蓬布下,把两腿伸直了在喘气。癞痢头一头灌着啤酒,一头大骂着:
“打了手印就是卖了身,有口气就得给我干!你给我死,死了我就饶了你!”
阿根也看定了死是唯一的解脱。从南洋来的路上,他一天天的数着已经挨过了多少班,还有多少班的罪在等他去受。他觉着一班的四个钟头,有四年那么长!每班就像死里走了几遭!死,就是死后下地狱,还能比这更苦?他在听到癞痢头最后一句话时,猛的站起来,一头扎下海去。
吃饭的人都停了筷,一怔,有人轻轻的“呦”了一声,便平静了,这也不新鲜,可以说趟趟船都有过,也从未有人当回人命事,只劳当头的对上头报一声:“一个升火跳了海……短了一个,坎仔补了缺。”就揭过了这一章。可是,这一回,众人刚要再动筷,癞痢头还要骂下去,又是扑通的一声响,大家便乱起来了,都拥到了船边,怎么会一连两个,又是谁?
那是水手富兴才,他不能算是老海员,才第一次走远洋,过这红海,他还不知道这里已葬过多少的升火,所以他看到有人落下海去,就不加思索的去救人。
他赴了没多远,便把正在浮沉着的阿根抓住了。他大声的呼喊着!这当儿来往的船正多,鬼子们再不能装着不知道中国人的事,于是船停了,打倒车,又停下来,在后尾看热闹的人们把绳抛下去,富兴才和阿根被救上来了。可是,就这一会儿的耽搁,后面那船,冒着浓烟,赶到前头到了。
一切又照常了,甲板上的人们在擦着汗,眯细着眼镜干活,火舱里的人们蒸着烤着的不是干活,是在挣命!只有舵面舱下的两个头脑有点反常,拉长了脸,不像素日那样悠闲自在。他们都挨了外国人的官腔,正盘算着把这受来的气装大一点往下倒,倒在底下人的头上。
太阳一寸寸的往西挪,由一团白热的铁斗化成了一个火红的血球,斗边天抹满了鲜血,映在海上也似通红的一溜血水。日班的人下了班在洗澡,洗一天的臭衣服。后尾蓬布下已有几个人在歇着,癞痢头正用那根粗藤条点着面对面的富兴才,骂着:
“我的人死就死了,跟你什么相干?你个杂种充好汉,下水救人,把船给拉到后头了,你又不能替他做班,他还是得死!你他妈的管闲账,今天就得教训教训你!”
癞痢头的藤条使劲劈下去,富兴才往旁一闪,一手抓紧了滕条,癞痢头喊了一声:“好小子,你敢造反!”他的三个打手抄了家伙一齐奔来!可是富兴才不等他们近身,早把藤条扔下海去,就手揪了癞痢头的脖子,把他提到了船边:
“咱们海里说去!”
打手和闲人都惊叫了,顶吓没了魂的还是癞痢头:
“老大,老大,放手!是我不对!”
富兴才并没放手,可回过脸对着那三个个子不大的打手,嘲笑的说:
“扔了那些废钢烂铁,去换太平斧头来,看我能不能一个个的把你们扔下海去!”
这句话倒帮了癞痢头的忙,他又摆出了头脑的腔调,虽然脖子还拑在富兴才的手里,他怒吼着:
“你们这些赤佬,我和富老大拌句嘴,也跑了来,给我滚开,真是赤佬!”
※ ※ ※
富老头停住不讲了,我还等着往下听。
“你赢了,以后呢?”我问。
“我输给了他!”
“怎么?”
“这些年来,舱面舱下我都干过了,从没干过‘头’,现在又迫得给他当伙计……”
我望着满天的星斗,打了个呵欠,凉风吹得我有了睡意。
“也不能不说年头改了!”富老头在絮絮的自言自语,“——得说是年头改了——改得太慢——还该再改一点……”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