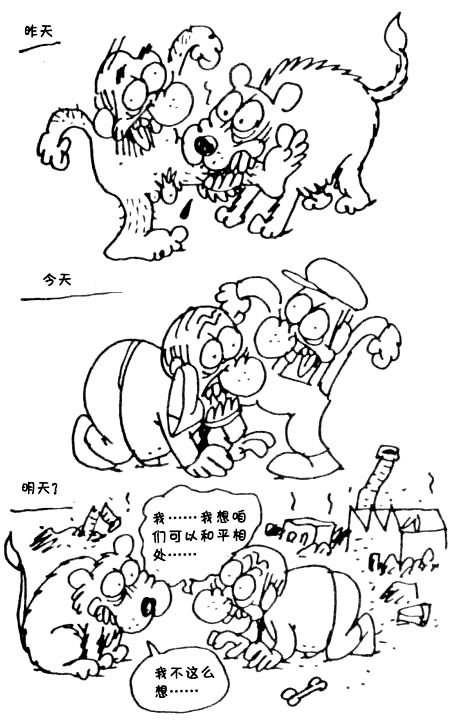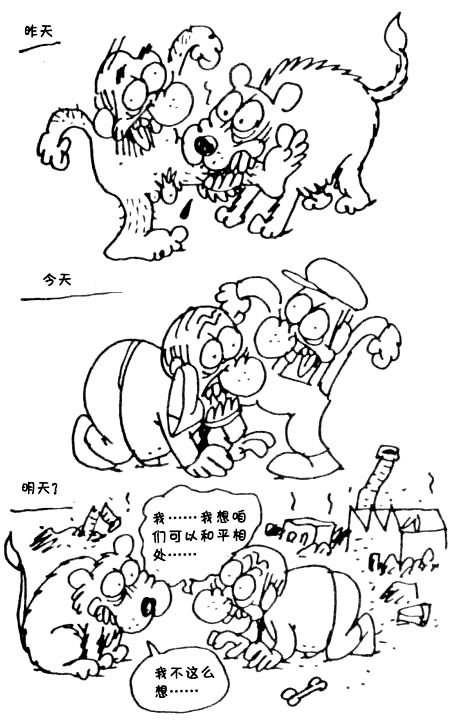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丹尼尔·本赛德 -> 《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2009)
第十章 为什么说马克思既不是环保天使也不是生产本位主义魔鬼?
就在《资本论》德语第一版出版的前一年,也就是1866年,着迷于创造新词的达尔文理论宣传者、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第一次使用了“生态学”这一词汇。在《普通生物形态学》中,他三次提到了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研究生物之间关系以及人类经济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
恩斯特·海克尔说:“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外部世界关系的科学。在这一外部世界中,我们可以以更为广阔的方式重新认识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的各个因素。”
进步的幻觉
马克思不是环保的天使,也不是一位被人遗忘的生态学先驱。不过在另一方面,虽然他经常对那个时代的生产本位主义式的热情表示赞赏,他也绝没有因此而毫无保留地去附和所谓”进步的幻觉”——这种幻觉在几年之后就受到了乔治·索雷尔的揭露。自从建立在剥削之上的生产方式使进步这一概念具有了双重性,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就不再是并行不悖的了。
正与之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草稿中写道:“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1]
因为“劳动生产率也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随着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少。在这些不同的部门中就发生了相反的运动,有的进步了,有的倒退了。例如,我们只要想一想决定大部分原料数量的季节的影响,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等等,就明白了”。[2]
关于资本周转的经济时间与自然再生的生态时间的不协调,林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漫长的生产时间(只包括比较短的劳动时间),从而漫长的资本周转期间,使造林不适合私人经营,因而也不适合资本主义经营。”[3]
当马克思意识到殖民所带来的痛苦以及劳动所遭受的摧残后,他对真正的进步的想象便超出资本主义之外了。他说:“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4]那真是一尊可怕的异教神像!
在这里,对进步神话的揭露来得既清楚又直率。而就在我们等待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之时,“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利。”[5]也就是说,在资本的统治下完成的进步,仅仅在于“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6]罢了。
人与自然
如果说遍布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草稿中的生态学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话,也并不妨碍它们深深植根于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与德国自然哲学的遗产之中。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与各种以劳动为中介的关系,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人“作为人的自然存在物”,“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有生命之物,“具有自然力、生命力”之物。作为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7]在这里,彻底的自然主义和彻底的人文主义合二为一。
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制约”与“限制”很显然伴随着生态学的推演,尽管“生态学”这个词并未出现。实际上,“制约”与“限制”正是一种对渴望奴役自然的普罗米修斯式欲念的抵抗;同时也使马克思年轻时在博士论文里对敢于桃战诸神的古希腊英雄们的热烈崇拜趋于缓和。
人类的存在首先是一种自然的存在,注定会有缺憾、有限度,但受到压抑时必须重振;人类也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因为自然既不在客观意义上也不在主观意义上,“直接同人的存在相适合地存在着”。所以,人类会历史地发展他的欲求与他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
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对自然的崇拜”在特定生产方式下发展了起来,于是自然变成了“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8]不管怀旧的浪漫主义者和空想的自然主义者们乐不乐意,蜕变成了某种有用之物的自然就这样跌出了神话,摔下了圣坛。
然而,人类社会的(人类学)自然限定并不会就此在历史的变化中土崩瓦解,因为事情与《哥达纲领》的作者们所宣称的正好相反:“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泉源。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9]
所以,自然并不能被归结成一个纯粹的社会范畴,因为作为“物质的所受的折磨”与“必要的媒介”的见证者以及“人与自然间的新陈代谢”的原动力,劳动充当着能量的转换器。这里的一个极重要的概念——“有机交换”或者“新陈代谢”,最初是借用自德国自然哲学,用以表达有机整体的概念,后来又经过了摩菜肖特等生物学家的发展,而马克思最早使用这个词是在《巴黎手稿》中。
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已经出现了对今天我们称之为“生产本位主义”的批判的梗概。其中,他提到了为了生产而生产的陷阱,消费发展不再与社会新需求有关,而是成为市场自发逻辑的必然结果的消费发展。不是为了满足需求,而是在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下进行生产,这实际上会导致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就这样,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中”了。
然而,“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也会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就像以前[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扩大生产范围一样。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10]
在那样一个时代,所谓“大堆的商品”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今天购物中心或者大型超市中的数量级,但马克思早已提前展开了对消费社会的批判,这说明他已经理解了利润的逻辑,并且认识到为了生产而生产的逻辑终将产生一种与人类需求发展不相符的、在数量上膨胀的消费。这样一来,对“物的新的有用属性”的正当探索便是以对地球的无限开发——这个词用得好——的形式进行的,仿佛这颗星球是免费赠予、任人宰割,以满足我们过分的贪欲的存在。
既然有着长期理论研究的支撑,那么马克思1856年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讲在今天看来所流露出的对生态学的忧虑便不应被看做是一次偶然的涉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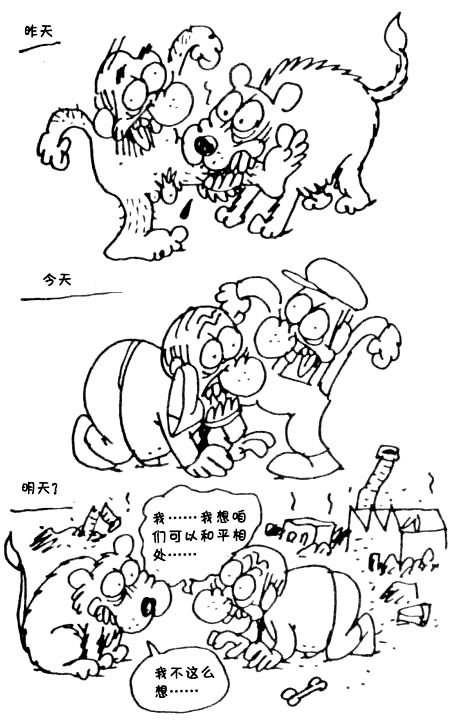
马克思讲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
“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岁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1]
一些人在指责生产本位主义时,出于这些疑惑,便同意宣称马克思是“无辜”的。然而他们却把“罪名”转移到了恩格斯头上:由于他的《反杜林论》,恩格斯仿佛有着重大的科学主义嫌疑。
然而实际上,恩格斯的立场与他的战友一样彻底:“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12]
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都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种两重性:一方面是发展,而另一方面是对其他可能性的消灭,也就意味着向单一方向的演进:“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化同时又是退化,因为它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的可能性。”他甚至已经隐约发现了存在于长久考虑(可持续发展)与市场的短视决定之间的矛盾:“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13]
超越极限的资本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了人类“受制约”和“受限制”的特点,他们却似乎并不打算从这些“自然限制”中继续推导出所有的结论。他们的保留可能与反对马尔萨斯[14]的论战有关,同时也包含了对热力学定律(尤其是熵的发现)可能使未日学说再次出现的担忧。
波多林斯基一事体现了争论的复杂性。1882年,一位乌克兰医生,谢尔盖·波多林斯基因肺病在法国蒙彼利埃疗养。他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能量在人类劳动产物中的积累方式的问题。
1880年4月8日,谢尔盖·波多林斯基写信给马克思,向他介绍“使剩余劳动的概念与目前占统治地位的物理学理论一致起来”的尝试:“人是一台机器。他不仅将热量与其他物理力转化为劳动,还可以将这一过程反方向实现,即将劳动转化为热量与其他必要的物理力,以满足我们的各种需求。所以我们可以说,人有能力通过他的转化为热量的劳动来加热他自己的铜炉。”波多林斯基正走在能量平衡理论的道路上。
1882年,病重的马克思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了,他就波多林斯基一事向他的“科学顾问”咨询。恩格斯赞扬了波多林斯基的作品的重要意义,但拒绝接受他所得出的结论。他说:“波多林斯基的东西我是这样看的:他的真正发现是,人的劳动能够比在没有它的情况下更长久地使太阳能保留在地球表面上并起作用。他由此得出的全部经济方面的结论都是错误的。”“波多林斯基离开自己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发现而走人歧途,因为他想为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寻找一个新的自然科学的论据,因而把体力的和经济的东西混为一谈。“[15]
就这样,在对波多林斯基的发现的重要性给予肯定的同时,恩格斯表达了双重的保留意见。首先是科学上的异议:万物不灭,即使我们不知道消耗掉的能源去了何处,总有一天我们也会重新发现它们;然后是认识论上的异议:劳动在物理上和在经济上的概念是不同的。恩格斯反对科学的那种“将自然科学理论应用于社会”的狂妄,所以他认为我们不能将经济学的内容转换为物理学的语言表达,反之亦然。
有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在意自然的限制。这一看法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16]事实上,马克思毫不含糊地揭露了过度消费以及“为了生产而生产”的做法。
首先,土地的有限属性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之一。“假如土地作为自然要素供每个人自由支配,那么,资本的形成就缺少一个主要要素。”[17]绝对限制与占有的概念奠定了对资本主义地租的分析。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写道:“如果富饶而肥沃的土地对现有人口和资本来说作为自然要素面存在,实际上是无限的;如果这种土地‘还没有被占有’——‘谁愿意耕种就归谁支配’,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会为使用土地付任何代价。”如果土地在实际上是无限的,那么“一个人对土地的占有实际上根本不排斥另一个人对土地的占有”。这样,“就不可能有任何私人的(也不可能有‘公共的’或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存在。”[18]
马克思所担心的,是高密度的农业会榨干土地的肥力,而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却不再能弥补“同样很重要”的“自然生产率”的降低。资本的投入(肥料的投入)只能拖延由资本主义城市化所导致的养料循环的中断。“自然的肥力是一个界限,一个出发点,一个基础。”或早或晚,资本会跌倒在自然肥力的限度上,这只是时间问题。恩格斯在刚刚22岁的时候就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表达了对城市化的忧虑,以及对厩肥(和粪肥)无法再回到土地中会导致养料循环中断的担心!
即便马克思没有继续推导出所有的结论,他依然一针见血地批判了作为资本固有逻辑的在量上的“无限化”趋势。而这种趋势的结果就是对有用属性以及质量的否定和忽视。
马克思写道:“对资本来说,任何一个物本身所能具有的唯一的有用性,只能是使资本保存和增殖。我们在货币上已经看到,作为价值而独立化的价值……除了量上的变动,除了自身的增殖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运动。这种价值按其概念来说,是全部使用价值的总汇;但由于它始终只是一定量的货币(在这里是资本),所以它在量上的界限是与它的质相矛盾的。因此,它的本性是与它的质相矛盾的。”[19]
为了对比,这里提到了历史上帝国时期的罗马。在这座城市里,价值成为了独立的“作为享乐用的财富”(也就是奢侈消费),居然“表现为无限的奢侈,这种奢侈甚至要使享乐达到想象中的无限的程度,竟要吞噬凉拌珍珠,等等”。在资本的积累中,价值“能保存自己,只是由于经常地越出自己在量上的界限”,” 发财致富就是目的本身”。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草稿中写道:“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0]
而马克思所憧憬的自由依然处在“人类本性”条件的限制之下。因此这自由必须节约被集结起来的力量,做到最低消耗,并建立起与自然进行理性交换的关系。而作为生产者的联合,这一理性的经济模式还有待于社会的定义。我们知道,可能的自由决不会是绝对的自由,而会受制于一种必然性,即作为一个物种从属于自然法则所带来的必然性。
广义上的劳动不是别的,正是将生命所从事的再生产以及生命所处的环境维系起来的新陈代谢。如果我们要彻底地废除这一限制,我们将同时中断生命的循环。不过,我们可以将这一限制极大地弱化,这正是人这种自然存在物的人性方面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写道:“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21]
[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第57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注。
[2]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篇。——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289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译者注。
[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译者注。
[4] 卡尔·马克思,《纽约每日论坛》,1853年8月8日。——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第69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注。
[5] 卡尔·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第一册。——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第26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注。
[6]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第823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译者注。
[7] 卡尔·马克思,《巴黎手稿》。——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20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注。
[8]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9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译者注。
[9]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9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注。
[10]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注。
[1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第58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注。
[12]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519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译者注。
[13]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522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译者注。
[14]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8-19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指出食物的增长呈算术速率,而人口的增长呈几何级数,这在未来可能导致灾难。著有《人口学原理》一书。——译者注。
[15]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第127、129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译者注。
[16] 参看《马克思、曼德尔与自然限制》,第113-128页,2007年版。——原注。
[17]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第41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译者注。
[18] 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册,第348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译者注。
[19] 卡尔·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第一册。——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22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译者注。
[20]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926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译者注。
[21]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925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译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