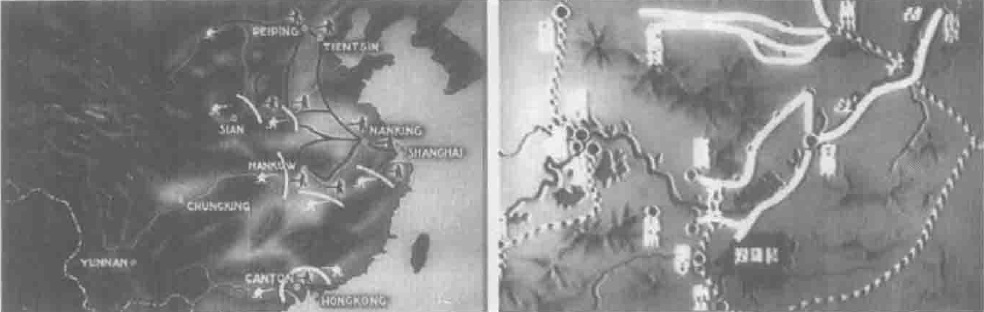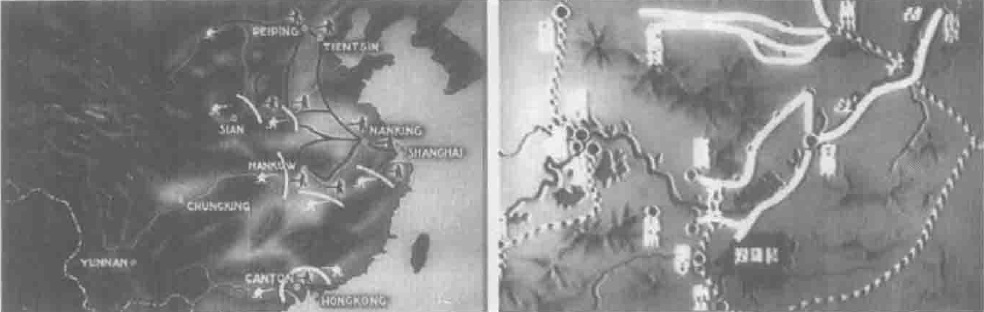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伊文思与纪录电影(1999)
一场战争的两种观点
——伊文思和龟井文夫
〔法〕基斯·巴克
程玉红 译 胥弋 校
“人们常常会问,为什么我们没有从另一方立场上也拍摄一部客观的电影呢?我唯一的回答就是,如果纪录片导演的作品之中包含有任何主动的、感情的或者艺术价值因素,他必须对法西斯主义或者反法西斯主义那样重大的问题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对于这些问题的争端他必须表达出自己的感情。考虑很简单的一种情况,当你置身于一场战争之中,你要从作战的一方到达另一方,你会被枪杀或者被抓进囚犯集中营——无论你是作为一名战士还是作为一位电影导演,你不能同时站在交战双方的立场上。如果有人想要那种“争端双方”的客观,他必须拍摄两部影片,假如他能够寻找到一位合适的导演,那么这两部影片就是《西班牙土地》和一位法西斯分子制作的某部电影。
——伊文思:《摄影机和我》 |
“没有一部纪录片可以是完全真实的,这样的纪录片是不存在的,因为社会的发展变化总是自相矛盾的。”
——保罗·罗莎:《纪录电影》 |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之后,中日战争开始进入新阶段中日战争的烙印“深深的留在新闻事业中”,这是一段很长的时期。虽然新闻片在意识形态对峙的双方都处于旺盛时期,摄影师们身处战争漩涡之中,但是,这些还是未能满足战争后方的需要。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和龟井文夫来到中国,他们各自站在战争对立双方的立场上进行着拍摄……
剧本是为充满战斗场面的战争片而准备的,但是,这仅仅是拍摄的影像:这些影像是为一部纪录片准备的,涉及到这场战争、真实的枪杀以及交战中的另一方。尤里斯·伊文思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拍摄了《四万万人民》,龟井文夫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拍摄了《战斗的士兵》。他们拍摄的都是单方面的、主观的影片。所以,如果纪录片像数学一样的话,依据前面引用的尤里斯·伊文思的话,我们通过观看双方的这些影片能够获得某种客观性……考虑到这种客观性,我们也许不会变得更明智,但是,我们回头看看这两部影片,就会明白他们如何从不同的视角来表达相似的事件,就会明白他们如何表现他们的事实,就会明白这些纪录片的真实是什么。
首先,我对影片进行较详细的介绍,接着使用一种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两部影片之中那些值得分析的瞬间,演绎导演的表现手法,引起观众的思考。目的不在于检验两部影片关于历史事实的精确性,而是比较两者如何传达他们对立的观点,尽管他们都有相似的影像。同时,我想谈谈纪录片与真实的不确定的关系,将纪录片与历史编纂学进行比较。
伊文思和龟井文夫在中国
龟井文夫在摄制《战斗的士兵》之前,已摄制另外两部关于“中国事件”的影片——日本人喜欢称之为“中日战争”。这些所谓的战争纪录电影受到日本后方的欢迎,因为人们有时候会在银幕上发现自己的亲戚或朋友,这一点在报纸上有广泛的报道。龟井是东宝电影公司第二制片厂的领军人物,该制片厂致力于纪录片制作,或者军国主义电影。在日本,那时候纪录片仍处于发展之中,导演深入到影片的计划、拍摄、编辑等整个创作过程中,龟井文夫被认为是最早的真正的纪录片导演之一。然而,他拍摄第一部“中国”电影《上海》的时候情况却发生了变化。1937年.他派摄影师三木茂(Shigeru Miki)前往上海,这位摄影师随身带着将要带回日本的影像资料的清单:“我强调,场景要吸引日本民众多愁善感的情感生活,就像黄昏的落日景象所产生的效果。三木茂忠实地拍摄了清单上的所有东西。”这肯定是一份特殊的清单,因为三木茂带回来的主要是“战争的残暴和哀怨的诉说”[1],这违背了日本政府的严格指令:
1)不要使军队受到嘲弄;2)不使用过度现实主义手法夸大战争的残酷性;3)不要摧毁那些有家人在前线的家庭的精神;4)不要鼓励寻欢作乐或者使享乐主义退化。
[2]
龟井文夫接受了这个挑战,把这些影像资料编辑成电影《上海》。这部影片受到观众和批评家的广泛关注,人们能够感受到影片中的含混之处,主要原因是受到影片资助(军方)方面的影响。[3]同样在《战斗的士兵》中,也能够发现类似的含混,对此在后面将会提到。
当尤里斯·伊文思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龟井文夫几乎在同一时间来到北京拍摄另一部影片。这成为北京城市的一幅画像,但是,与其说这部影片是“战争纪录电影”,不如说它是“城市交响曲”,因为影片表现的唯一对象是战争本身——或多或少是明确的。他写到:“我的同事认为,《上海》是一部‘悲剧模式’的纪录片,而《北京》很容易被当成一个爱情故事。”[4]更重要的也许是这个事实,他本人不仅仅满足于编辑,而是接下来支配着影片的真实方向:他亲自加入到影片的拍摄中,并且亲自编辑影片。在当时的日本纪录片制作中,这是相当新颖的电影制作方法,后来(1940年)在他和摄影师三木茂之间(关于《上海》和《战斗的士兵》)就纪录片中的创造性引起了有趣的争论。龟井文夫认为:
“摄影师看事物仅仅通过寻像器。他们就像蒙着眼罩的马。掌握着摄影机,这是必然的。这就是为什么导演是必要的,是为了看到摄影机后面的世界和旁边的世界。”
[5]
1938年夏天,当龟井文夫带着三木茂来到中国拍摄《战斗的士兵》的时候,伊文思已经带领着自己的摄制组来到中国:约翰·弗诺(John Ferno)和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同年2月,当龟井文夫在北京拍摄的时候,伊文思他们抵达香港,继而飞到汉口,为拍摄后来的影片《四万万人民》做准备。伊文思刚刚在美国完成并且成功地宣传了影片《西班牙土地》,他很快又从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中获得灵感。
有趣的是,龟井文夫虽然有政府的资助,他在拍摄影像资料方面有相当大的自由度,相比之下,伊文思的独立制作却遭到国民党官员的严格控制。他们不愿意伊文思去前线,特别是共产党控制的前线。[6]龟井文夫一回到日本,就遭遇到审查制度——在电影审查制度的背景中,无论如何会删除掉某些重要的部分。所以,尽管龟井文夫能够得到他想要的影像资料,但是,在那个时期《战斗的士兵》从没有公开发行过,1941年,龟井文夫被捕。据诺尔斯(Nornes)说,政府对龟井文夫的控告持暧昧态度,关键可能是对龟井职业生涯的总结,被他的传记的自由主义修正和官方的恐慌提升了。[7]伊文思的影片《四万万人民》公开发行时,却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但是,伊文思却不能拍摄他所想要的东西。海伦·范·东根剪辑了这部影片,并使该片与众不同。
在这个阶段,我们关注这两部影片的一些前后关系是有益的,诸如:是谁制作了这部影片?目标群体是哪些人?动机是什么?概括地说,两部影片有同样的主题。然而,《四万万人民》是一个居住在美国的荷兰人拍摄的,《战斗的士兵》是从一个日本人的角度拍摄的。两者都是战争纪录片,具有同等重要的宣传价值,两者都是由纪录片的开拓者所拍摄:伊文思是一位国际纪录片制作的先驱人物,龟井文夫是日本纪录片的先驱人物。两部影片在结构和影像风格上非常类似:两者均呈现出战争造成的破坏。两者都展现了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中国人,但是伊文思更清楚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悲惨生活;两者都使用地图和字幕表达他们的故事,但两者都没有展现多少真实的战争场景——虽然龟井文夫的电影有字幕解说(有人批评说,它没有展现战斗的士兵,而是睡觉的士兵)。他们都很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观点自然相互对立。不过,两者在人物方面有些许不同,可从其不同的目的解释说明:《四万万人民》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令人鼓舞的影片.提高中国人民的斗争意识,阻止美国向日本出口钢铁材料(将会被制成炸弹),最终筹集资金来支持中国人民。《战斗的士兵》是赤裸裸的宣传片,目的为了巩固国内人民的支持,告知日本人民,他们的亲友正在中国为了“正义”的事业作战。伊文思的影片中,他把“和平群众的人道”与“日本的军事机器”并置起来。龟井文夫遵照政府审查部门的指令:
总的来说,策略是将世界描绘成被划分为:“那些从现状中寻求利益的国家”与“那些力图带来新秩序的国家”。这样就产生像“八纮一宇”的说辞(“征服世间的四面八方,置诸于一个屋顶之下”),一种适用于全亚洲的革命输入。[8]
《战斗的士兵》一开始,龟井文夫明确提出了“新秩序”。随后,我们会发现更多的这些并置关系,但是,现在它充分地说明,动机的差异导致了方法的不同:为了筹集资金,最好伴随着一个不公正的强烈感情的故事,而不是坚守国家或者超国家的政治问题。龟井文夫不需要去筹集资金;他的主要目标通知人们回家。日本国内观众渴望“来自战争的最新的可信的声音和景象。几乎人人知道某个人在前线,因此,人们的兴趣集中在战斗的过程,军队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日常生活等,这些是热切的和个人的。当观众看电视时注意到银幕上的一位爱人,他或者她就会关注这个画面以后的一连串影像。这些最生动的‘荧幕上的团聚’的场面被写在报纸上[9]”这样,龟井文夫影片的信息品质远远超过了最终的煽动性品质。
头脑中带着这种信息和实践的束缚,我们反问自己,人们能够想象到两部影片所代表的真实性或者可信度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吗?从中我们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客观现实”?在回答类似问题之前,为了明确分析的理论基础,我们不妨看看研究方法。
一种解释的迂回
当代思想中,现实的本体论依据已经变得令人质疑。特别是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现实的再现是核心要务,关于这个主题已有许多辩论。对于纪录片来说.情况是一样的:现实的价值由纪录电影再现,是对现实本身的模糊状况而言么?结果,伴随着“纪录片现实”的评估,我们无法逃脱后现代的教条,很久之前,尼采已经提出:“没有事实,只有解释。”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进一步扩展了这个表述:
“事实不是事件,它本身给予一个目击者有意识的生活,而陈述的内容意味着表现……事实可以说是通过使其从一系列文献中脱离出来的过程建构的,我们可以反过来说,是它们建构了事实。建造(通过一个复杂的纪录片程序)与一个事实建立(在文献的基础上)之间的相互作用,体现了对历史事实特定的认识论地位。正是这种历史事实建议的特点……决定了附属于事实的真实和虚假的模式。”
[10]
这一点,我的看法,不应该导致这样的结论,后现代主义者关于历史的态度:“是由对它的叙述、发现和真实要求的否定”[11]构成的。在我看来,其目的是要把真实放置于一种不同的语境之中,特别是有意识的语境中,正是在这种语境中它们产生了自己的意义。因此,当这些叙述、发现和真实要求被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时,它怎么能产生其他的意义呢?
特别是在纪录片中,在电视新闻节目中,我们看到真实是事物的核心。对于这一点的简单否定,将会妨碍我们理解和解释这些节目及他们所谈论的事件。尼采的论断“真实的世界终于变成一个寓言”[12],这不会得出我们无法依赖寓言的结论。恰恰相反,它仅仅是我们必须建立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的参照:
“我们从媒体和人文科学中所接受的世界的影像,尽管存在着不同的层次,但是,这不只是一种‘现实’不同的解释,即无论如何是‘假定的’,而构成了世界的非常客观性(……)它对认识到我们称之为‘世界的现实’是‘神话’多样性的语境,这是比较有意义的——人文科学的任务和重要性在于使用这些术语来准确地讨论这个世界。”
[13]
在此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战斗的士兵》和《四万万人民》作为构成世界客观性的叙述的一部分和目前状况下,中日战争的客观性。在这篇文章开头的引文中,在本质上并没有远离格安妮·瓦特姆(Gianni Vattimo)上述客观性的哲学立场。
尽管两部影片都论述到某种现状,一旦影片完成准备上映,这就成为一种过去的现实。所以,我们可以在纪录片和历史编纂学之间,得出某些相似之处,它们都针对一种从前的现实。一方面,这种先前性强调现在与史学家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它强调过去和研究对象的缺失。纪录片也表现实际上不存在的事物,它只是通过影像和声音来表现。史学家像纪录片导演一样在描绘——制造现在——过去缺失的东西;再现过去是保罗·利科在《记忆、历史与遗忘》中主要的研究对象,描绘记忆与历史编纂学之间的相似之处。对于现象学的含义,他侧重于记忆、以及过去缺失东西的再现功能,把记忆功能的现象学问题延伸到“抵达过去”到史学领域以及“真实性”问题。现实的再现,由历史的文本呈现,是真实的么?这个问题导致了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在文本中体现的现实的本体论地位,以及表现这种现实的可能性。实现本体论的现实是可能的吗?现实是什么?我们如何确定这种缺失现实再现的真实性?这些问题(也)导致参照的问题。纪录片的参照是什么?因为,涉及到历史编纂学和/或纪录片,现实作为表现现实是有意义的,意味着真理和真实的问题:在历史编纂学和纪录片中,参考,只有在它参考世界和没有参考世界时才有意义;换句话说,当我们在真实的现实和虚构的现实之间加以区别的时候,它对于历史学家和纪录片导演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也许更甚之对他们的读者们和观众们。
为了给我们的解释学方法一些哲学依据,给现在的迂回增加一个迂回,并且简单介绍一下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也可能是重要的,特别是关于“现实”和“世界”的概念。那些害怕凉水的,可以跳过下一个段落。
……
任何可能的世界的史实性限定了参照物的布景。但是,任何可能的世界只能由一种的刻意的对象构成,所以,任何与这种可能的世界相关的思想从一个现世存在的辩证法中涌现出来:在那里世俗是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通过存在,世界被构想出来。这不只是世界的本体论和现象学的游戏,而对涉及到世界的每个再现的我们的现实的概念有重大影响。在历史编纂学和纪录片中,世界或多或少被呈现为前后连贯的实体。这些再现创造了它们可能的参照物的布景,但也可能参照其他可能的世界。所以,这些世界招致一种可能的世界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使任何连贯的解释(可以被看作其他可能世界的构成)产生出杰作。通过分析《战斗的士兵》和《四万万人民》,我们可以偶然发现矛盾,但同时在彼此之间和我们对电影主题的认识之间,创建一种互动。
在纪录片和历史编纂学中,同样在小说中,世界通过一种文本呈现给我们,这种“文本的世界”,用保罗·利科的说法,拓展了参照和意义的概念。
它的意义,是理想对象是目的所在,对话语来说,这种意义是纯粹内在的,它的参照物是真实价值,它的要求是抵达现实。
[14]
这种抵达真实的诉求可能会被我们上面的思考所质疑,但是,当分析的文本指的是现实(任何可能的现实)时,对启动现实仍然是有效的。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把这些对现实和可能的世界的反映考虑进去,能够使文本中的参照物被进行分析。这种“实施”不过是努力寻找可能的参照物的正确布景,使其与正确的可能的世界相匹配。
《四万万人民》、《战斗的士兵》与纪录片导演的转变
在《记忆、历史与遗忘》中,保罗·利科分析了“历史学家的目的”,在一段缺失过去的再现中,历史进行了重构。他将其放置于史学编纂操作的“纪录片阶段”。纪录片的阶段是意义的轨迹,一个认识论的过程,其中通过三个阶段:从证据,经过档案到纪录片证据。所有这些阶段涉及到历史事件和地理位置,或再现的事物的状态(他们的历史性)。这种纪录片的阶段只是前三个阶段,由解释和理解的阶段和再现的阶段来完成。在最后阶段中,再现被当作史学编纂操作,一个过程。[15]
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一套时间和地点,是他想要描述的从前的现实相关联的。这种有经验的地点和时间的这里和那里的总体,将被放置于这个时间和地点的系统,其中涉及到绝对的此时此地,主体被剔除了。已经建立的时空体系远未完成:历史学家必须选择。哪些要描述的时间和地点(事件)是最重要的呢?选择的第一阶段很大程度上依靠历史学家的解释。我们可以把这比作研究阶段,或者法国人在纪录片中更准确地将其称为“定位”:选择什么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涉及到特定事件的时间和地点。这有非常多的含义,但很可能是必然的含义,因为它不可能证实和保存所有东西,同样,也不可能用1:1的比例制作一张地球的地图:它让利科进行以下的沉思:
“如果历史编纂学是所有存档的记忆最先的,如果随后的被历史知识的认识论所占据的认知操作来自于存档的最初姿态,那么,历史学家关于时间和空间的突变,可被看作是这种存档姿态可能性的正式条件。”
[16]
这种“历史学家的突变”隐含在史学编纂的纪录片阶段。它从归档过程的第一步开始,建立起一种连贯的时空体系。在纪录电影(电视)制作过程中,我们能够认知到这种同样的突变过程:导演与/或者他的研究成员从无条件限制的事件范围中选出事件来。所有这些事件的特征就是它们时空的连贯性。当不同的事件被放在一起挑选时,一系列事件的新的连贯性被假设和规定了。事件的选择,及更重要的,在此阶段过程中,省去其他的事件的决定,确定了历史的突变。
我们应该把历史学家与纪录片导演区别开来,因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那些变成档案的东西(记录或写成的目击实录),最后已经被我们的纪录片导演伊文思和龟井文夫再现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电影是他们的目击实录,受到了叙事性的处理。然而,一般来说,从感觉和证词到档案文献、文件证明和它的解释,这是一条轨迹,应该令历史学家和纪录片导演在使用“资料源”时谨慎行事:
“存档的时刻就是进入史学编纂操作的写作时刻。证据最初是口头的。它被倾听,听到了。档案被写下来。它被阅读、查阅。在档案馆里,职业的历史学家是读者。在被查阅或者建档之前,有东西被存档了。”
[17]
这里保罗·利科暗示的是,档案资料已经被挑选过,它也许是不完整的,和不可信的,就像同证据也许是不完整的、不可信的一样。虽然如此,我们作为旁观者,可以承担历史学家的角色,把这些影片当作我们的档案资料,努力去确定它们的日期和所发生的地点,给出我们解释性的处理,最后完成史学编纂操作。我们用其他的资料源(自传、档案、新闻影片、历史著作),能够将这些事件进行重构,虽然这不是我们这里的目的所在。最重要的是意识到历史学家和纪录片导演的突变,原始素材所经受的。
《四万万人民》和《战斗的士兵》都在一种现实中题赠给他们自己的,这种现实就像发生在“现在,我们摄影机前面”一样。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日期。确定事件发生的地点不成问题.幸亏在两部影片中所呈现的动画的中国地图(勾绘出差不多相同的军队路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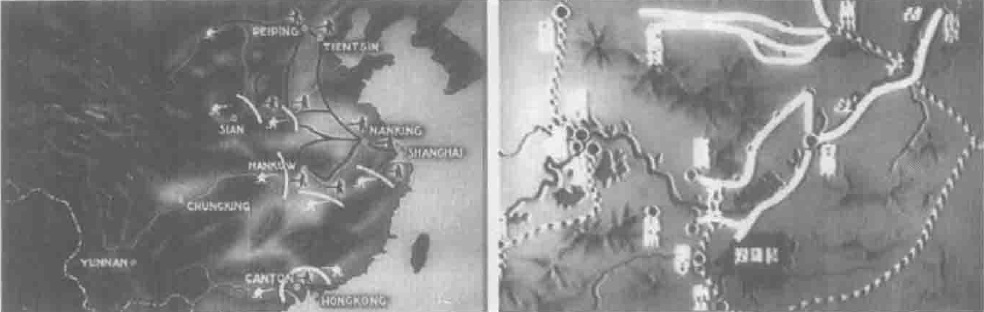
《四万万人民》中的地图 《战斗的士兵》中的地图
幸亏有其他的原始资料(和/或我们的历史知识)和电影提供的信息,我们不难确定两部影片的拍摄时间:两部影片中都有一个大事件,成为其最重要的吸引力。伊文思关注“台儿庄战役”(1938年4月),龟井文夫的影片却以武汉战役(1938年10月)结尾。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拍摄的不是同一个事件。虽然,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两部影片的信息非常值得去分析——我们可以说明,伊文思在中国拍摄他的影片,时间是在1938年春和初夏;而龟井文夫在中国拍摄他的影片《战斗的士兵》,时间是1938年夏末和初秋(我们也知道,1938年春,他已经到北京了)。
从一开始,片头的字幕中,伊文思明确地揭露了实情,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或者“人道”对抗“一种法西斯攻击”。这种攻击的残暴通过关于日本轰炸造成的死亡数字统计加以强调:列举了城市和死亡人数(上海:20,000;南京:10,000;武汉:15,000;广州:20,000……),以这些因轰炸导致破坏的影像、死者的尸体、废墟、人们的恐慌,以及为伤者提供的救助来说明。这些清楚的影像后面,紧接着是那些难民,“到西部去:古老的土地”。令人感到有趣的是,看到龟井义夫在他的影片里.也是很早就展现了中国难民的影像,但是,展现这些的理由当然是截然不同的:伊文思想要使观众相信,“中国人民需要获得支持和帮助;龟井文夫争辩,虽然经历了大萧条,但是,中国人的生活很快就会恢复正常。至少,这至少显示这样的信息。但是,我们稍后会在龟井文夫的影片中,看到比这个更加模糊不清的东西。片头字幕声明之后的第一条字幕:“现在大陆经历了残酷的劳动的折磨,一个新秩序将会诞生。”[18]
在影片《四万万人民》中,伊文思宁愿回到先前的秩序,即使是最近的秩序。同上所述,在开头一连串的描述之后,影片全面地展现了中国丰富和历史悠久的文化,展示古代国王的坟墓、古老的雕像,关于孔子和老子,展现了辽阔大地上多样性的风光,包括长城和马可波罗的路线。伊文思希望看到,由孙中山“中华民国的华盛顿”所效仿的近代的秩序重新建立起来。虽然有古老的文化,“一个新的声音从人民运动中涌现出来”,影片中紧接着是最新的成就,诸如:铁路、农业水利和工业(“钢铁、煤炭和棉花”)。伊文思谈论敌人是很细致入微的: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有着渴望——食物、工作与和平。是他们的统治者带来了战争和侵略。影片从这时开始,展现更多的是战争的影像:和平示威,国民委员会,领导人之间的战略讨论,蒋介石夫人,受伤的士兵,军事装备,以及影片将要结束的时候一些战役和作战的士兵。
实际上,在《战斗的士兵》中也是这样的:主要是在影片的结尾,我们真正地看到士兵在作战。如同在《四万万人民》中一样,之前我们看到类似的影像,军队调动,军事装备(坦克和大炮),战地医院,一个指挥官发布命令——影片中一个较长的,明显的摆拍场景之一。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士兵在战场之外的日常生活:休息的士兵,水的净化,一个士兵阅读一封从家里写来的信,马靴的修补以及更多休息的士兵。
两部影片都描绘一个敌人:《四万万人民》中的“日本侵略者”,《战斗的士兵》中的“抗日武装力量”。但是,在后一部影片中,日本军队审问中国士兵展现了战争的荒谬:“你多大岁数?——30岁你有小孩吗?——有两个孩子。你想回家吗?——我想回家。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农民。”尽管字幕中有其他的评论,龟井文夫影片中的许多影像含蓄地展现了战争的荒谬与残暴。一些字幕是给天皇和英勇上兵的颂歌,其余的给人的印象是每个人在战场上,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渴望很快结束所有这一切:“这里,汹涌的战火已经熄灭,”或者“士兵们绝望地战斗,希望形势很快就回到正常的状态(武汉战役之后):“这天,已经在后街上,就像在焦土策略中看到的一样,移动着求生的意志”紧接着是中国大人和小孩的画面。

《战斗的士兵中》中,不忍目睹的雕像
似乎《战斗的士兵》比《四万万人民》更加含糊不清,而且超过了它自己的字幕所暗示的。关于这一点,有几个例子,片头字幕之后立刻开始,让人相信“在现场的士兵有美好的愿望”。我们看到一个在神旁边祈祷的男人,燃烧的房子,孩子们在观望,一个中国男人的特写镜头——他们的父亲?这个场景之后是难民和一些中国文化的残存物,正如一个用手蒙着眼睛的雕像,它似乎在说:“这简直令人目不忍睹……”影片一开始是战争导致的破坏场面,这是由日本人造成的。这不是一个令政府满意的片头,他们不想展现战争的残酷。
通过观看这两部纪录片,我们可能会认为,伊文思像喜欢中国人一样,也喜欢日本人,但他不喜欢日本统治者;龟井文夫非常同情中国人民,他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没有说谁会赢得战争……)。而且,我们看到,《四万万人民》对它的解释和所表现的事件没有提出问题:对于一个美国(或欧洲)观众来说,它依然是一部令人鼓舞的影片。另一方面,《战斗的士兵》可能会毫不隐讳地用它的语言,它的影像对整部电影的陈述增添了许多含糊不清。虽然影片有几次展现了一面日本旗,却从未象武汉城墙上的国民党旗的特写镜头那样大(当然,那面旗不会留在那里)。这与伊文思在《四万万人民》中展现的台儿庄城墙上那面几乎看不见的国民党旗相比,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有一面共产党的旗帜,那么它会是多么大呢?
关于马、眼罩与真实
《战斗的士兵》中的另一个场景是象征性的,像那个不忍目睹进行的战争的雕像一样。在一条空旷的乡间道路上,我们看到一匹马——生病或者受伤——慢慢地但平稳地双膝跪下,最后倒下了。这个画面是以下面一条字幕引出的:“有很多次,当快速追赶的时候,病马会落在后面。这种时刻,士兵的心中在哭泣,但是,在战争进行当中却爱莫能助。”正如马克·诺尔斯(Mark Nornes)讲述的:
“这种简单的场景——一条字幕和一匹马——在日本电影史上是最著名的镜头之一。它使战争纪录片的传统暴行去掉了艺术化,隐藏的空间的深切的悲伤,有力地浮现出来。”
[19]
伊文思与龟井文夫二人,他们的影片所表现的他们的世界的真实现实也许并不多,但是,他们不得不为此说些什么。这大概是纪录片与新闻片的区别,或者与历史文献——档案的区别。保罗·罗莎在关于纪录片与新闻片区别的一段有趣的谈话中说:
“……它们二者,以各自的方式,处理原始的素材。但是有相似的结尾。它们接近和解释材料的方法截然不同。纪录片方法的本质在于真实材料的戏剧化。这种剧情化的行为导致一部电影的叙述不忠于现实。我们必须记住,大多数纪录片只忠实于它所描绘的一种观点。”
[20]
这种观点与保罗·利科的“历史学家的目的”相一致吗?不完全一致,但是,它竭力去进行比较。保罗·利科描述的纪录片阶段是一条通过史学编纂操作的不同阶段的意义的轨迹。正在讨论中的是一种过去现实的意义.参照的是所有这种阶段的操作。我们已经看到过去的事实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在历史编纂学和纪录片中都一样,这决定了最终适合于它的事实的价值和准确性。一本历史文本或者一部纪录片,指的是一系列呈现事实的事件。在《战斗的士兵》和《四万万人民》中就是这样。事实的呈现和事件的再现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文件和事实在假设的形式中彼此互相依赖。它们是历史知识的基础,尽管所有的历史变化不得不被考虑进去:伊文思和龟井文夫都没有使用中日战争的全部信息和全部事件,因为有几个原因。全部利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们或许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许不想去了解和识别理论上可以识别的每件事情。除了他们的摄影师之外,伊文思和龟井文夫也有他们的眼罩。但是,他们的电影给观众戴上了眼罩,仅仅通过展示和讲述,就这样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对所有可能的事实进行选择。
最初的感觉及其证言之间的距离变得很大,将这些东西转变成电影使得这种差距变得更大了。因此,在纪录片阶段中所证实(检验)的是事实,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事实就像史前古器物一样。那么,真相对于历史学家和纪录片导演来说,是只能去接近的东西:
历史的意图性意味着,历史学家的建构有被重构的勇气,或多或少地去接近有一天会是“真实”的东西,无论什么困难,终会被我依然要求的“坚持”解决。
[21]
当我们加入海德格尔的真理如同“无遮蔽”的概念时,我们可能认为保罗·罗莎的真实,是一种非常充分的说明,即使对一般意义上的存在:
因此,不隐藏的存在有等级和层次。“真理”和“真实”对每个人来说,没有停留在与自我一致,不同的视角毫无变化。它们是到处都不一样的,并且不为所有人共同享有的。(……)每个真理有它的“时间”。最终,它是一种教育的符号,对隐瞒某些来自知识的真理,并对它们保持沉默。真理与真理不仅仅是相同。
[22]
借助现象学的意图性概念,保罗·利科的“历史学家的目的”的观念,伊文思和龟井文夫由他们纪录片表现的观点,我们可以断定,我们在兜圈子。幸好,海德格尔安慰我们说,解释学循环是意义的结构:“认为这个循环是要处理的问题(……),从根本上是曲解了理解。”[23]让我们希望这至少是真实的。
[1] 引自Peter B High,《帝国的银幕:15年战争中的日本电影文化,1932—1945》,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2003年,p103。
[2] 同上,p99。这些指令和审查制度与1939年的电影法一起变得非常严厉,在Abe Mark Nornes《日本纪录电影,明治时代直到广岛》,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3年,pp61-72。
[3] 关于电影《上海》,我们可以在Nornes和High的等作中看到更详尽的描述。
[4] 引自土本典昭的一次访谈,发表于1987年,High转述,p106。
[5] 引自Nornes的著作,p157。
[6] 关于电影摄制组在中国工作的“外交”影响.见汉斯·舒茨《危险地活着:伊文思传》第11章,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2000年,同时见伊文思自传《摄影机和我》,七海出版社,柏林,1969年。
[7] 见Nornes的书,pp177。关键在于他的传记,举例来说,他从1929年到1931年曾在苏联逗留,在那里学习无产阶级的电影制作。
[8] 见High的书,p97。
[9] 见High的书,p93。
[10] 保罗·利科《记忆、历史与遗忘》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4年,PP178-179。
[11] Robert A. Rosenstone《过去的未来:电影与后现代历史的起源》见Vivian Shobchack编《历史的持久性:电影、电视与现代事件》Routledge,New York/London,1996,p202。
[12] 尼采《偶像的黄昏》,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p20。
[13] Gianni Vattimo《透明的社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巴尔的摩,1992年,pp24-25。
[14] 见利科的书,p113(我的译文)。
[15] 利科的书,2004年,pp231和167-174。利科在其书中整个第二部分里详细说明了这一点,在标题“历史-认知论”之下。
[16] 利科的书,2004年,p148。
[17] 同上,p167。
[18] Nornes对《战斗的士兵》做了详细的叙述,包括字幕的英译,均引自其中;Nornes,pp161-174。
[19] Nornes的书,pp166-167。
[20] 保罗·罗莎《纪录电影》,Faber and Faber出版社,伦敦,1935年,pp133-134。
[21] 利科的书,2004年,p262。
[22] 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Gallimard出版社,巴黎,1988年,p32。
[2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p153。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